那还是百多年前的事儿,正值树叶飘落、百草泛白的时节,天气冷得厉害! 在俺们孔庄子,来了一个要饭的。此人五十来岁,身材高大,生着一双黄眼珠子,脸盘宽阔,模样看上去极其凶狠,任谁见了都会心生畏惧。他上门乞讨时,既不称呼人,也不吭声,只是伸手比划,那意思再明显不过,要是不给吃的就坚决不走,说话还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叽里咕噜的,咱这片儿的人大多都听不懂,于是大伙都喊他“蛮子”。
当时天气已然十分寒冷,别人都早已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可他依旧身着单薄的衣衫,被冻得牙齿直打颤。无奈之下,他只好钻进村东的场屋,窝在草堆里。有时候,他一待就是一两天,任凭别人怎么轰,都不愿离开。村里众人私下猜测,这人多半是犯了王法。为何这样说呢?当时清朝盛行留辫子,可他头上却没有辫子,只留着帽缨子。要知道,以前那些犯了法的人,不是用绳子捆绑,而是将绳子穿过辫花牵着。所以大伙推断,他肯定是剪掉辫子后逃到了这里。我们这个地方紧挨着海边,地势低洼,村庄稀疏,几十里地都难见一户人家,官差就算来查,也很难顾及到这儿,倒的确是个藏身的绝佳之地。虽说村上人都明白他可能犯了案子,但这事儿与自己无关,也就没人打算向官府告发。

天愈发寒冷了,村上有位姓孙的老奶奶,一生乐善好施。见这“蛮子”整天窝在自家场屋不出来,实在可怜。毕竟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冻死呢?于是,孙奶奶东拼西凑,找来了一些布料和棉花,赶忙为他赶制了一身厚实暖和的棉衣,而后送了过去。这举动可不得了,那“蛮子”顿时感动得落了泪,“扑通”一声趴下,“冬冬”地磕了两个响头,嘴里还接连喊了好几声“干娘”。孙奶奶深受触动,便认下了这个干儿子。
既然认了干亲,自然要当作亲人对待。孙奶奶把他领到家里住下,关心地询问他姓甚名谁,老家在何处。他回答说老家在江南九江府仁山县骆塘,名叫童子师。其实啊,他真实身份乃是捻军梁王张宗禹。在那个时候,他又怎敢吐露实情呢?从那以后,他便隐姓埋名,在这个家中安顿了下来。
彼时,孙家是个大家庭,三十多口人共同生活,日子过得还算宽裕,多他一个人也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而已,几个干兄弟对此也都没有意见。他要是愿意干点活儿就干些,不愿干也没人强求,反正大伙也不指望他,毕竟看他样子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孙家有个儿子叫孙喜章,那年二十出头,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夏天时,他到大洼里打草,吃住都在那儿。有一回,他吃了没熟透的瓜做的疙瘩牛,结果肚子难受,疼得厉害。家里人花了不少钱,请了好几位先生,抓了好多服药,可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这一病就是好几个月,疼起来时,小伙子在地上直打滚,原本好好的一个人,眼瞅着就要不行了。
张宗禹得知此事后,赶忙对干娘说:“干侄得的是淤积病,我能治好!”一家人听了,既惊喜又有些怀疑,毕竟对他还不太了解。但孩子病到这般田地,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说不定真能治好呢! 于是,张宗禹开好了方子,差人去韩村抓药。可方子里有硫磺、巴豆和砒霜,药量又大,药店的人顾虑重重,不肯抓药。张宗禹听闻后,顿时火冒三丈,说道:“我去!” 说罢,便带着人再次前往韩村。等他把药抓回来时,天色已然漆黑。
张宗禹非要亲自熬药,可一看到药里有那么多砒霜,全家人都吓坏了,心里满是担忧,毕竟虽说认了干亲,可对他的过往一无所知啊! 但张宗禹可不管这些,硬是把干娘和干兄嫂都推出门外,插上房门,还用杠子顶住。任凭外面怎么呼喊,干娘如何责骂,他就是坚决不开门。

好不容易,张宗禹把药熬好了,小心翼翼地给病人灌了下去。没过一会儿,病人就发起烧来,浑身滚烫得像个火炉,嘴里不停地哼哼着。这可把一家人吓得不轻,张宗禹却镇定自若地说没事儿。接着,他打开门,扛着铁锨匆匆跑到村北大坑,用力铲开冰层,铲起一锨薄泥后,便急忙往回跑。一家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只见他把薄泥敷在病人的心口、手心和脚心上。没过多久,泥就被烤干了,他再揭下来重新糊上,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奇迹发生了,这时病人说肚子没那么疼了,只是感觉有点憋得慌,想走动走动。这一上厕所可不得了,肚子里的东西倾泻而出,就像把肠子都清空了一样,仔细一看,里面果然有当时吃的疙瘩牛!这简直是起死回生啊,大伙都对张宗禹的本事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张宗禹一下子名声远扬,消息在十里八乡越传越远,越传越神乎,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就这样,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郎中。
不过,想请张宗禹看病可不容易。他平日里总是待在屋里,很少出门。他的屋子也很特别,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四处都被堵得严严实实,轻易不让人进去,谁也不知道他在屋里捣鼓些什么。有人来请他看病,都得先找干娘,只有干娘同意让他去,他才会动身。他给人看病从来不收钱,但要是有人给他送酒和点心,他倒是乐意接受。回来后,他会把点心送给干娘,酒则留给自己喝。他酒量极大,喝酒就跟喝凉水似的,端起一大碗,“咕咚咕咚”,一仰脖子就喝完了。一喝醉了,要么大喊大叫“杀————杀———”,要么就放声大哭。干娘知道他这毛病,担心他酒后惹出事端,有时就会把酒藏起来,或者干脆把他锁在屋里。
张宗禹不仅会看病,还懂看风水,能看阴阳宅。记得他刚到村子不久,有一天村里请来了一个外地风水先生。他听说后,便跟着干侄孙玉同去了坟茔。在那里,他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地方是龙脉、水脉,茔地怎样的走向才好……好家伙! 说得头头是道,比那专业的风水先生还厉害。干侄惊讶不已,心想:“啊嗨—你居然还有这本事?”一问之下,张宗禹坦诚说道:“不瞒你说,我以前就是干这行的!”这一下,可不得了,就像草洼里突然来了只金凤凰。大伙这才知道,张宗禹不仅医术高明,还精通风水,从此再没人喊他“蛮子”了,都尊称他为“童先生”。孙玉同更是当即花了不少钱,给他买了一架罗盘,还跟着他学习。正所谓“自古近处菩萨远处灵,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从这以后,请他看风水、看阴阳宅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一天,孔庄子突然来了个黑大汉,自称是来找张宗禹的,说是表兄弟。二人一见面,都激动得落下泪来,接着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话,可旁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人自称叫阎五,随后便在村上住了下来,给人打短工。他饭量极大,主家每顿饭给他端多少,他就能吃多少,每次吃完饭,盆碗都干干净净的。有一回,主家蒸了一锅窝头,心想就算他饭量再大,也不可能全吃完吧?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往院子里一蹲,一个接一个地吃不一会儿,那一大锅窝头竟然被他吃得精光,连咸菜都没就。主家见状,着实被他这惊人的饭量吓住了,寻思着不能再留他了,于是之后每顿饭就只给他两三个窝头。阎五干了没几天,实在忍受不了这饭量限制,就对主家说:“您就让我吃顿饱饭吧,我保证给您好好干活!”主家这次蒸了两大锅不掺菜的纯面窝头,阎五一口气就吃了一锅半,这才满足地说吃饱了。随后,他先去与张宗禹见了一面,接着扛着大衫镰就下了洼。打完一趟草后,他扔下镰刀,便不知去向了。可他打的这趟草,主家竟然拉了两大车都还没拉完。
张宗禹在孔庄子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不知不觉间,他已从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变成了七十多岁的老者。这些年来,他凭借自己的医术为这一带的百姓治好了许多病,大家都对他十分敬重,每当提起“童先生”,无不竖起大拇指。
有一天,张宗禹买了几嘟噜酒,罕见地请来了几个干兄弟以及村上几位关系要好的人一起喝酒。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孙家的人都清楚,他以往从来没有主动买酒请过客,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酒过三巡,张宗禹缓缓开口说道:“我就要走了,这些年多谢你们的关照了!”众人以为他是打算回老家,便说道:“您都七老八十的人了,年轻时不回去,怎么这时候想着要回老家啦?”张宗禹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回老家,而是自己快要走到生命尽头,要归西了。大伙都知道他一喝酒就爱说胡话,以为他又在发酒疯,所以都没把这话当真。
又过了几天,张宗禹对干侄说:“我这就要走了,可不能让我光着身子走呀!”干侄赶忙应道:“那是自然。”随后,便专门派人去韩村拉回来一口质地不错的松木寿材。张宗禹看到寿材后,十分满意,这儿敲敲,那儿拍拍,最后还躺进去试了试,不大不小,恰恰合适!
四五天后,张宗禹躺在炕上,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看样子不行了。这时,他让人把全家人都叫到跟前,说有重要的话要说。没过多久,全家人都到齐了。
张宗禹缓缓开口,说道:“我叫你们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件隐瞒了二十多年的事。我不叫童子师,也并非江南九江府人,我真正的名字叫张宗禹,是安徽涡阳人,我其实是捻子的头领。当年天王洪秀全封我为捻军梁王。这么多年一直瞒着你们,实在对不住。还有,那年来到这里的阎五,他是我的部下……” 接着,他详细地把自己兵败在平,而后侥幸逃生的艰难经过讲述了一遍。一家人听后,无不惊愕万分!
张宗禹最后虚弱但又坚定地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村南张家地的北边两道之间。让我的脚冲着西南方向的老家,如此便足够了!”话刚说完,他双腿一蹬,便溘然长逝了。
从这以后,人们才终于知晓张宗禹的真实身世,明白了他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捻军梁王。孙家对他的葬礼丝毫没有含糊,操办得十分妥当。自那以后,每年到了上坟除草的日子,大家都不会忘记到他的坟前,虔诚地祭奠一番,缅怀这位曾经在孔庄子留下诸多故事的传奇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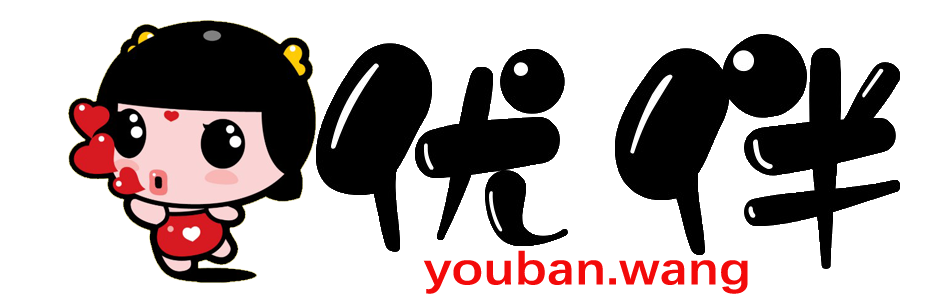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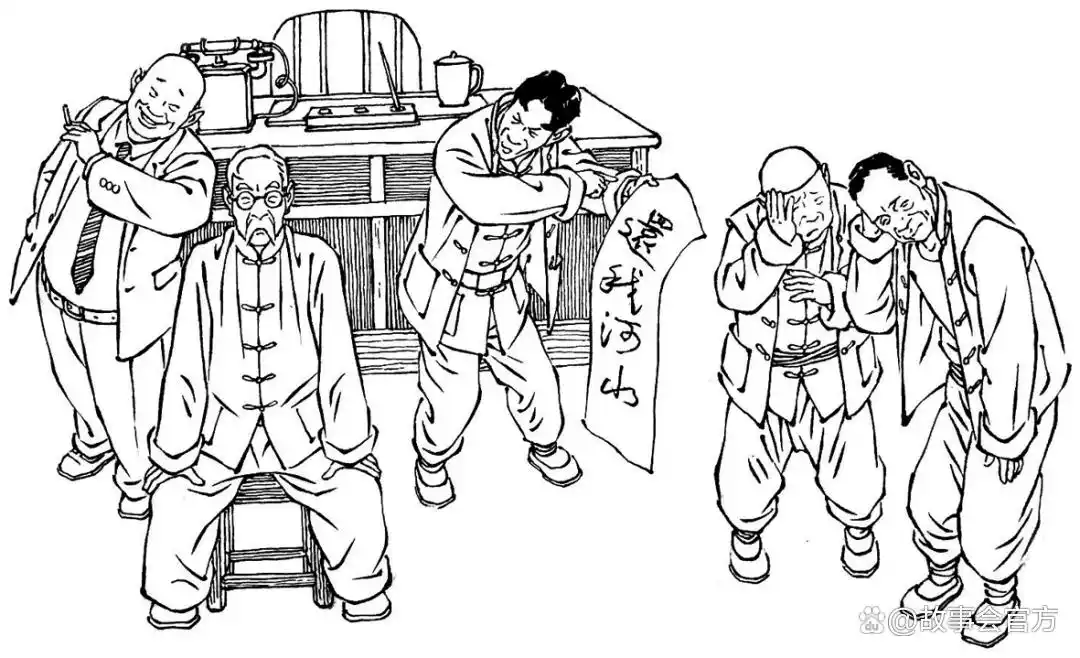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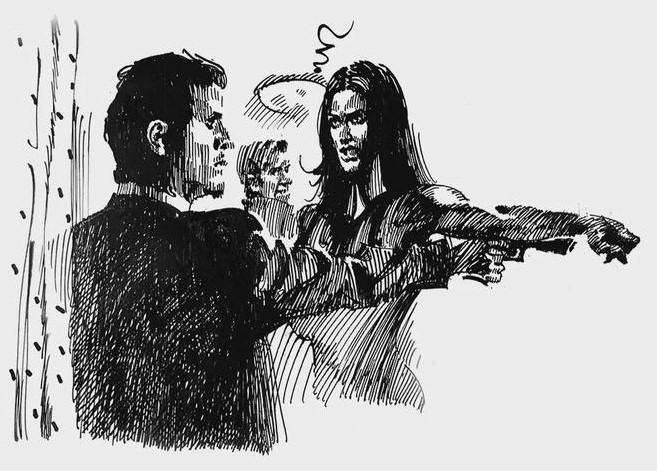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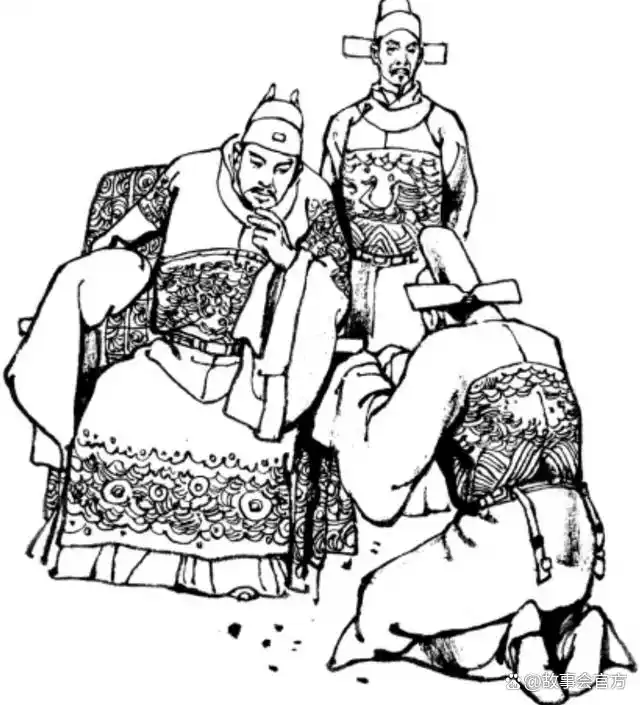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