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进腊月,小王庄就像年下一样热闹起来。各家的热炕头上,堂屋地里,结满霜花的玻璃窗下,风快地传播着一条新闻:王老大的儿子小水和王老大的闺女小珍,订亲了!
小珍子是四岁那年跟着她妈“走道儿”过来的。娘俩嫁爷俩,虽不犯法,却不合俗,而且还有一个不雅的称谓,叫“爹公娘母”,总难免叫人说长道短。不过,这回却是例外。全村百十户人家,家家赞叹,户户感慨,仿佛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小王庄的人,这些年,经的见的多了,平常的事,犯不上浪费眼泪疙瘩。偏偏谈起这段兄妹姻缘,连一些最讲旧礼儿的老人,也不断地撩起衣襟抹眼角。
嗨,人们又想起王老大来了。
王老大活着的时候,没谁惦记他。他是小王庄出名儿的笨人,手笨、嘴笨、脑子笨。有一年,县剧团下来组织赛诗会,一位女演员包他们小组,要求每个人都单独登台来一首。女演员听说他笨,特意给他挑了一首最简单的,可他还是左教右教背不出,老师急得满脸通红,学生直拿袄袖子擦汗。没办法,只好破例编个集体节目,叫他混到里头,跟着嘎巴嘴。
谁想上了台,别人张嘴他闭嘴,人家闭嘴他嘟囔,惹得观众哄堂大笑,全组狼狈退场。那女演员气得鼓鼓地指着他说:“你真是个笨人!”还有一回,队长永绪的媳妇到他屋来,给他说对象的事,正说着,怀里孩子尿了,队长媳妇赶忙把孩子放到炕上换裤子,一边随口叫他关上门,哪知道,他老哥竟咕咚咕咚跑出去,把大街门给插上了。队长媳妇笑得前仰后合,弯下腰,点着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哥,你真是个笨人!”
笨人干活不藏奸,不耍滑。可是历来评先进、选模范什么的,他都沾不上。队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除了派民工、秋分红,各类表格上很少见着他的名字。晚上开会,差不离回回都是他先到,坐在队部大炕的灯影后面,津津有味地听到完。可是队长一发脾气,就说:“敲钟开会,为什么全村没一个准时来的?”那口气,似乎王老大不算小王庄的人。一来二去惯了,人们只有在逗乐子时,才会提到他。什么“王老大叫门———笨到家!”还有什么“王老大演节目———跟着混!”又有什么“王老大换尿布———该关街门啦!”等等。
小王庄的人们开始严肃地议论王老大的为人处世,是在他两次组织家庭之后。
王老大的对象挺难找,不是人家嫌他太笨,就是他嫌人家太灵。直到三十出头了,才由队长永绪趁外出开会的机会,给他寻摸了一个姑娘。两人见过一面之后,很快就登了记。队里批给他一块地基,大伙七手八脚,垫土的垫土,打坯的打坯,不几天就盖起了三间土坯心、砖包角的海青瓦房。说说喜期临近,谁成想王老大节外生枝。
他的新房隔壁,住着一户人家。两口子结婚七八年没孩子,那男的跑了一趟大同,抱回来一个小男孩。说也怪,自从抱的孩子进了门,那女人竟一连生了两胎。有了亲生的,抱来的成了累赘,受尽了虐待。乡里乡亲的看不惯,队干部也多次对那公母俩进行教育,无奈人要是不地道,凭谁也劝不好。王老大很怜惜那孩子。路上遇见了,总要拉到井台旁,给他洗洗小脏脸、小黑手,往怀里塞根麻花什么的。有时候,还给他捉个小黄雀儿,编个鸟笼子玩。
如今,跟这家人成了邻居,天天听那院里不是打,就是骂,大人吼,孩子哭,四五岁的孩子,又抱柴禾,又看小的,成天眼泪汪汪,焦黄枯瘦。这天,夜里下过一场小雪,他起来扫院子,忽听那边屋门“哐当”一响,孩子被推了出来,说是不让小的抓笼子里的雀儿,得“冻冻”。大冷天,那孩子光着头,趿拉着两只大人鞋,穿着袖子短了半截的小薄袄,进不去屋,哭喊着拼命挠门,这真像挠了王老大的心!他再也忍不住,翻过院墙,抱起那孩子,冲屋里吵了起来。
王老大吵架也透着笨,吵了半天,其实颠来倒去还是那半句话:“新社会啦,你别太什么了!”倒是那个狠心的婆娘,反像占了多大的理,连篇叠句,辣气尖声,吵了个没完。什么“多管闲事”啦,“挑唆孩子跟俺分心”啦,“逢傻必奸、笨人心毒”啦!那男的更是风风火火,把个鸟笼子扔到院里,连同王老大给孩子新逮的“吱吱红”,一脚踩个扁。
周围的乡亲帮着王老大数落他们几句,谁知那女人竟倚疯撒邪,发泼叫号:“扳着不心的牙,说凉快话谁不会?俺们家的孩子就这么养活,瞧不惯的领去,谁要给谁,把他供在佛龛上俺不管。退俺们二百块钱的本儿了事!积德的,行善的,领啊,领啊!”王老大气黄了脸,抱起孩子奔了队部。
王老大非要这孩子不可。特别是听说那两口子即将迁居关外,他不能眼瞅着孩子叫他们带走。队长永绪劝他,是不是等未婚妻来商量一下?王老大自信多余。人心都是肉长的,商量不商量的,还能有别的主意吗?那两口子一看王老大真要孩子,以为得了发财的机会,漫天要价,什么“吃食费”、“穿戴费”,外加“操心费”,算来算去,竟算了五百元!最后还是永绪作主,一百五十元把孩子断给了王老大。那两口子除了心病又得钱,自是欢喜不尽,一家人急忙忙搬往关外去了。
孩子安安稳稳睡到了王老大的炕头上。可是未婚妻呢?不用说,当时办登记是永绪开的介绍信,这回又是永绪搬动大印,给他们办了解除婚约的手续。王老大头一次成家,媳妇没娶来,先“娶”来一个儿子。
对这桩事,小王庄的人们有的赞成,有的摇头,争相议论了很久。
王老大自管按照他笨人的思路行事。他给孩子改取了个庄稼名,叫小水。他抱着小水到诊所看病,到供销社扯布量衣,又求队长媳妇纳底子做鞋。他自己则是一天两顿,蹲在灶前,做了稀的做干的。每当小水扳着他的肩叫一声“爸爸”,他的心里都要“呼啦”地热一下。这个笨汉子,不会流泪,也不会用五官的移动来表示自己的感情,他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一些,嘴里含糊地答应着:“嗨嗨!”
赞成与摇头之争尚未平息,转年开春,便又传来了王老大二次成家的消息。
那时,“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刚刚解散,人们正挨度着可怕的春荒。一天王老大进山砍柴,正路过大北峪沟口的探头砬子下面,忽听一阵哭声从上方传来,抬头一看,竟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斜挂在从峭壁石缝里伸出的树枝上。王老大撒腿跑上崖顶,又着石缝溜下去,解开捆柴用的绳子,把孩子拴在自己身上,一步步往上登。到了上边一问,才知道孩子是为了摘那几粒隔年酸枣。
这时候,一位妇女,怀里揽个吃奶的,手里拽个刚会走的,呼哧呼哧跑过来,叫了声:“珍子!”就再也跑不动了。小女孩扑过去,抱着她妈腿哭起来。王老大很生气,冲着那妇女喊道:“你这个当妈的!”女人一愣,似乎感到委屈,但并不剖白,只是用感激的目光温顺地望着他。突然发现了他脸上有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便连忙从怀中裹孩子的小被上撕下一条布来给他擦,又赶着给他拍打身上的土。
王老大怒气未息,还想教训她一顿,尚未开口,却一眼看到她脚上穿的孝鞋,便呆住了。他又看到那个刚刚被他救下的珍子,正往刚会走的小弟弟嘴里一粒一粒地塞酸枣,王老大不说话了。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净面窝头,递过去。那孩子妈妈不肯接,低声说:“大哥,你还得干活!”王老大动动嘴唇,把窝头放在她怀里的孩子身上,抹身走了。
这个女人是谁呢?她的孩子为什么饿成那样?王老大从不爱打听人,这回却怎么也搁不下。他抱着小水到队长家串门,因为队长媳妇的娘家就在大北峪。这位弟妹,平常一个人在家对着墙还得练嘴呢,何况有人来问?不等王老大问完,话匣子早打开了。原来这女人叫大翠,当姑娘时就是出名的老实疙瘩。嫁个男人,倒也般配,谁知头年又死在浮肿病上。为了丈夫的病和死,她拉下了不少饥荒,连那点点口粮都卖了一半。现在,她背着一身债,又带着三个张嘴要食的小崽,再寻主吧,谁要?不寻吧,可怎么过呢?
是啊,她可怎么过呢?———王老大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思谋着,直到小鸡子叫。
笨人也真有邪的,第二天他竟然抱着小水,悄悄跑到大北峪,闯进人家寡妇家里,硬把几张钞票,摔到了那个心情慌乱的女人的面前。一个月后,他又公然到队长家来求媒了。队长媳妇吓了一大跳,一个劲地嚷嚷:“笨哥,你可别胡说八道,你再想想,再想想!”王老大吭哧憋肚,还是那半句话:“新社会啦,咱们都得什么点!”
小王庄又一次轰动。这回,赞成派急剧减少,摇头派大大增加,更有一些难以入耳的尖刻议论。
有的说:“八辈子没见过女人,叫这么个娘们迷惑住了,替死鬼拉套去吧!”
有的说:“可怜小水,后爹娶后娘,出了尿窝进屎窝!”
庄稼人毕竟心肠热。说归说,总不能袖手旁观,还得想办法劝说。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挤进王老大的小院,又叹着气鱼贯而出。人们在村口围住了媒人,指令她不许穿线。
队长媳妇虽然嘴快,却处处听丈夫的。队长一口咬定:这门亲事,可订!他命媳妇突出重围,往返三次,做成了大媒。他又亲自套了一辆白马大车,把那四口接进了小王庄。
队长永绪是小王庄公认的灵人。兴许是相反相成之故,这个出名的灵人却偏偏佩服那个实足的笨人。起小儿的俩人一块玩,灵人总取出招儿的,笨人总取出力的。不过一到坎上,灵人总要看看笨人的神色,想从那里讨到一点什么启示。实在,灵人懂得笨人那颗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心。即如眼前,在笨人心底的一团美意不为众人理解的时候,如果不是队长兼灵人出头张罗、呵护,恐怕他连新娘都接不进门呢!
大翠低头进了小王庄,像是请进来一台戏,立即被各种各样的目光团团围住。一些长舌之妇、好事之徒,专拣饭时去串门,要看看粮稀米贵之年,新人是怎么给自己的三个亲崽和一个后儿盛粥!有时,他们还拉住小水问:“你妈打你不?”“你妈给妹妹、弟弟做好吃的啦?”
使这些无聊的人失望的是,小水和小珍他们,成天手拉手乐呵呵地跑进跑出,“咱爸”“咱妈”喊得山响,大翠拿个贴饼子给几个孩子掰,总是妹妹让哥哥,哥哥让弟弟,根本分不出两窝儿的!
大翠深知,在这一米度三关的饥年荒月,王老大收留她们母女四人,这个人该有多么热的心肠,多么大的勇气!于是,她也把一个善良的女人心中蕴藏的一切深情、美意,倾献给自己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小水。三十多岁的王老大,何曾受过这样的温情?何曾有过这样和谐、妥帖、井井有条的家?他心满意足。
他似乎觉得,自己过了这些年,专等的就是她!他常常禁不住久久地在灯下端详他的女人: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挽个髻,乌黑的眼睛,白净的下巴,总是闲不住的一双厚厚的手……看着看着,他那被山风吹就的水泡眼变得迷惘起来,厚嘴唇颤颤地,小声问:“你,还走吗?”大翠先是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后来又舒眉展眼地笑了,说了声:“傻子!”便甜甜地投到他汗浸浸的怀里。
小王庄也出过几个高中生,都是读过外国小说的,他们叹息说:这是怜悯和感激,算不得爱情哟!也许,王老大和他的大翠还没有那么高的程度,反正是,这两个身负生活重压的庄稼人,就是如此相依为命地结合了!
饭桌上清汤寡水,热炕上恩爱夫妻。大翠除了尽心照顾好四个孩子,难免要额外关心一下丈夫。为这,还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呢。有一天,四个孩子都睡下了,大翠从被窝垛下面掏出一个用毛巾包着的贴饼子,悄悄塞给丈夫。王老大接过一看,火了,冲着她大声嚷嚷:“你这是干啥?”气得大翠第二天跑去找队长媳妇诉说。
队长媳妇打趣地说:“咳,他那是疼孩子,舍不得吃!他疼孩子,不就是疼你嫂子吗?你呀,急啥?慢慢来,教他……”姐妹俩吃吃地笑了。事情到了队长媳妇嘴里,自然传得快。从此,小王庄关于王老大的俏皮话里,又添了一句:“王老大吃贴饼子———慢慢来!”笨人听了,嘿嘿一笑。
不过,终归是两个人的口粮,一下子分到六个碗里,粥稀了,人瘦了。再加上替大翠还账,光棍汉多年的存项花光了,日子够紧巴的。队长永绪在会上提出给他家一点救济,却被王老大拒绝了。他自有办法。
笨人王老大是砍柴人里的状元。“镰刀快不快,全凭胳膊拽”,人说王老大上山不带镰刀,一天也能拽它五六百斤山柴。山里人有句话,叫“驴二驴二”,说是一头壮实驴最多也只能驮二百斤。人说王老大背的柴,一头毛驴驮不动。平时蔫头耷拉脑的王老大,一背上捆满山柴的梯架,精神头就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走累了,把木棍拄在梯架下面的横梁上,两腿稍作弯曲,让山柴的分量落在木棍上,就能美美地歇一歇。新婚后的王老大,每当这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声梆子腔哩。这,还不算他的看家本事。砍柴人最称道王老大的“绝招”,是他能够背着二百多斤山柴很轻松地伏下身子咕咕噜噜喝一气清凉的泉水,胡茬上挂着冰花,一溜小跑,追上前行的同伴。
村里人管王老大那双轮胎底、实纳帮的山鞋叫“山羊蹄子”,意思是只要山羊能够上去的地方,就休想挡住王老大。“阎王鼻子”、“小鬼脸”是大北峪里的险道,使一般的砍柴人望而却步,笨人王老大偏爱用他的镰刀给“阎王”、“小鬼”们剃头刮脸。因为那里山柴厚密,砍一天顶三天。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天天讲路线,办啥事还有点灵活性。靠了这点灵活性,王老大农忙下田,农闲背山卖柴,尽管他的大翠又给他生了一个小五,他还是不向队里伸手,咬牙渡过了难关,还居然添置了奢侈品———一架小小的收音机!晚饭后,一家七口围着匣子听评戏、听相声,觉得小日子有滋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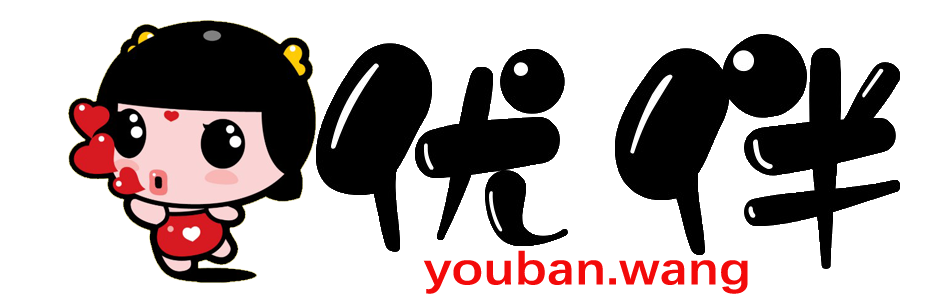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