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候,洛宁县有个叫顾长会的后生。爹娘走得早,他是被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二十岁这年,他娶了镇上商户家的女儿陈氏,小两口没靠着长辈,自己琢磨着做买卖,后来竟盘下了个货行,日子渐渐红火起来,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富户。
陈氏是个本分女人,进门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可顾家长辈盼着抱孙子,直到陈氏快三十岁时,才终于生下个儿子,取名顾同。这下可把顾长会的爷爷奶奶乐坏了,逢人就说“顾家有后了”。老两口没愁多久,笑着闭了眼,走得安详。
又过了十年,顾长会的两个女儿都出了嫁,婆家都是殷实人家,日子过得滋润。陈氏看着女儿们安稳,儿子也长到十岁出头,心里踏实,可没承想,一场急病把她带走了。
顾长会忙着货行的事,顾同才十一岁,家里里外外没个女人操持总不是办法。一年后,他续娶了邱氏。邱氏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顾林。这下好了,货行生意越来越兴旺,家里又添了人口,街坊邻居都说顾家是“人财两旺”,羡慕得很。
七年后,顾同成了家,媳妇是潘掌柜的女儿潘氏。潘家在城外镇上开杂货铺,潘掌柜为人正直,跟顾长会是多年的老朋友,这门亲事也是顺理成章。可没过多久,潘掌柜就过世了;顾长会本就因操持生意累坏了身子,受了这打击,也病倒了,半年后就咽了气。巧的是,潘氏刚生下个大胖小子,顾长会临终前看到孙子,笑着闭了眼。
说起来,邱氏刚嫁过来时,顾同才十一岁。她待这继子跟亲儿子似的,顾同也敬重她,一口一个“母亲”叫得亲。所以顾长会一走,顾同就请邱氏当家:“母亲,家里还是您做主妥当。”
邱氏红了眼眶,叹气道:“你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我一个妇人,哪懂当家?你品行端正,又会做生意,肯定能把家业撑起来。我呀,就帮着管管家务,再照看你弟弟就行。”
顾同见她实在,便应了:“那儿子就先担着。”话虽如此,家里金库的钥匙还是让邱氏管着,每月的账目也让账房刘先生报给邱氏——这是顾长会在世时定下的规矩,顾同不想改。邱氏推不过,只好接了。
顾同是个天生的生意人,脑子活,人也正。自从他掌家,货行的生意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三年工夫就成了洛宁县最大的货行,连周边县城的商户都来打交道。
这时候顾林也十一岁了,性子外向得很,天天上蹿下跳,书院的先生三天两头上门告状。邱氏没辙,只好让他别上学了,跟着哥哥去货行学本事。顾同疼弟弟,可也不想他学坏,管得严,该骂就骂,该罚就罚。没想到顾林偏偏服大哥,对生意也上心,学东西快得很,顾同看在眼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家里和睦,兄弟和睦,本是兴家的好兆头,可架不住有人心术不正,在背地里捣鬼。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顾同的媳妇潘氏。
潘氏有个哥哥叫潘茂,兄妹俩没随爹潘掌柜的正直,反倒随了娘邓氏——贪财、吝啬,还爱计较。潘茂这性子做生意,能不赔本吗?潘掌柜过世不到两年,杂货铺就被他折腾关门了,还欠了一堆亲戚的债。顾同念着亲戚情分,替大舅哥还了债;后来邓氏哭着求他,他又让潘茂去货行帮忙。
没过多久,账房刘先生要回乡养老。潘氏就跟顾同吹枕边风:“相公,账房的位置空着,让我哥顶上吧?他跟着学了这么久,肯定能行。”
顾同知道潘茂的性子,不太乐意,可架不住潘氏天天说,又想着都是亲戚,便点了头。
潘茂进了账房,看着顾家的家业,眼睛都红了,总想借着做账捞点好处。可邱氏心细,每笔账都盯得紧,他愣是没找到空子。
这年初秋,潘氏回娘家看邓氏,邓氏留她住了几天。夜里母女俩睡一个被窝,邓氏摸着女儿的手叹气:“我听你哥说,家里还是你婆婆当家?”
潘氏撇撇嘴:“说是相公当家,可金库钥匙在婆婆手里,账目也得报给她——公公在世时就这么定的。”语气里的不满藏都藏不住。
邓氏眼珠一转,拍着大腿道:“傻闺女!做娘的哪有不偏亲生儿子的?你婆婆要是在账上动手脚,偷偷给顾林攒钱,你们夫妻俩不就吃大亏了?再说了,货行都是你相公辛辛苦苦撑起来的,顾林才多大?将来家产一分,你们能占着啥便宜?”
潘氏心里早就这么想过,跟顾同念叨过几次,每次都被顾同训一顿“别瞎想”。她叹了口气:“有啥办法?相公孝顺,我多说一句都不行,只能顺其自然了。”
邓氏没再接话,可从那以后,潘氏每次回娘家,她都念叨这事。日子久了,潘氏心里的不满就像野草似的疯长起来。
十月初七是邓氏的生日,顾同要去外地收账,没法亲自去,提前备了厚礼让潘氏捎去。邱氏也备了份体面的礼。
当晚,邓氏拉着女儿的手,声音压得低低的:“你小叔子再过几年就要成家,到时候肯定得分家。就算不分,你婆婆也得拼命给顾林捞好处。你相公挣得再辛苦,将来还不是便宜了别人?”
这话正说到潘氏心坎里,她急道:“那咋办?相公是个死脑筋,根本不听劝。”
邓氏凑近了,声音像蚊子哼:“你娘我懂点相面——你婆婆眼带桃花,没说话先笑,嘴角还偷偷往上翘,这是贪淫的相。她才三十多,守着这么大家业,日子太舒坦,难免动心思。你家不是有下人吗?想个法子让她出丑,到时候就算你相公不在意,她也没脸再管家里的事了。到时候你接手管金库,想帮衬你哥还不容易?”
潘氏听了,心里竟有点欢喜,可又犯难:“这法子是好,可我婆婆住在后院,平时不怎么出门。家里就两个男仆,一个是看门的福叔,另一个是花匠葛叔。婆婆爱花草,倒是常跟葛叔打交道,可葛叔都六十多了……”
邓氏一拍巴掌:“笨!找个由头把那老头子赶走,让你哥寻个年轻俊朗的花匠来,提前打点好。我保证,你婆婆肯定扛不住。”
潘氏从娘家回来,满脑子都是这事。正愁怎么换掉葛叔,老天竟帮了忙——葛叔中了风,瘫在炕上起不来。顾同念着主仆一场,给了葛家一大笔钱,让他回家养老。
没过几天,潘茂就给顾同引荐了个人,名叫李红,二十七岁,长得眉清目秀,说以前在大户人家当花匠,手艺好,一年前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娘才辞了工。顾同满脑子都是生意,没多想,又是大舅哥引荐的,便爽快答应了。
十天后,李红进了顾家。顾家的花园在偏院,跟正院隔着一道门,晚饭后福叔会锁门,第二天清早再开。园子里有四间小屋,李红就住那儿。
这李红的手艺确实比葛叔还好,把花园打理得花团锦簇。邱氏看了高兴,常去花园逛逛,跟李红说说话。
邱氏原本是个本分人,顾长会在世时,她一门心思照顾孩子、操持家务;顾长会走了,她又忙着带顾林,没空想别的。可这两年顾林跟着顾同学做生意,天天不在家,她身边没了人,难免觉得孤单。李红长得俊,嘴又甜,说话时总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勾引,慢慢就把邱氏心底那点沉寂的心思勾了起来。
一年后的初夏,两人在花房里越过了界限。欲望这东西一旦开了头,就像决堤的洪水,收不住了。从那以后,李红常常趁夜溜进邱氏屋里,都是三更去、四更回——这时候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加上李红手脚麻利,竟没人发现。
其实每次李红走后,邱氏都后悔得不行,可事到临头,又总忍不住。
潘氏早就等着这一天,想按计划揭穿,早点拿到金库钥匙,起初并没打算置邱氏于死地。可邓氏更狠:“等你相公在家,他八成会瞒着。不如等他外出时再闹大,让街坊四邻都知道。你婆婆好面子,肯定活不成。到时候顾林没了靠山,家里不就全听你的了?”
潘氏起初觉得太毒,可在娘和哥的撺掇下,心也硬了起来。
没多久,顾同带着顾林去陕州收账。邓氏和潘茂、潘氏立刻开始谋划。
顾同走的头四天,潘氏每晚都偷偷盯着后院,可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看丈夫就要回来,她急得满嘴起泡,连着四晚没睡好,精神头差了不少。
第五天吃过晚饭,潘氏安排儿子睡下,自己歪在床上想歇会儿,结果不小心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被尿憋醒,一边起身一边嘟囔:“千万别误了时辰。”
刚上完厕所往回走,就听见外面传来三声更鼓——三更了。声音刚落,她就看见一个人影从花园围墙翻进了后院。
潘氏心里一阵窃喜:“老天不负有心人!”她悄悄往后院走,见邱氏屋里的烛光昏昏暗暗的,像是用纱巾挡着,隐约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影子在晃动。
机会来了。潘氏蹑手蹑脚走到前院,隔着门对福叔的住处小声喊:“福叔,快起来!咱家进贼了!”她知道福叔耳朵灵,不用大声,免得惊动后院。
果然,福叔很快就拿着灯笼跑了过来,急道:“少奶奶,有几个贼?”
“我就看到一个影子,不敢确定。您年纪大了,家里又都是妇孺,相公和二少爷还不在,快喊人吧!”潘氏故意装作害怕,声音都在抖。
“好!我去叫隔壁周家兄弟!”福叔说着就开了大门。周家就在隔壁,兄弟俩是做豆腐的,这时候也该起来忙活了。
一切都按计划来。潘氏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突然放声大喊:“来人啊!有贼!快来人啊!”
深更半夜的,这喊声穿透力极强,不光家里的厨娘被惊醒,左邻右舍也听得一清二楚。
福叔带着周家兄弟冲进院子,三人直奔后院。潘氏跟在后面。
屋里的李红和邱氏被喊声吓懵了。李红衣服都来不及穿,就穿着条衬裤,光着上身,抱着衣服往外跑,正好被福叔和周家兄弟堵在门口。
潘氏假装吃惊地“啊”了一声,赶紧转过头去。
福叔一看这情景,脑子飞快一转,赶紧打圆场:“没事没事,是误会!”周家兄弟也反应过来,跟着福叔扭头就走。
可顾家平时人缘好,潘氏这一喊,不少邻居都跑来帮忙,有几个跑得快的,正好看到李红从邱氏房里出来。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顾家主母跟花匠私通了。
潘氏假惺惺地跟大家说“是场误会”,求大家别外传。多数人真心为顾家着想,嘴上答应了,可架不住有长舌妇,比如邻居张大娘和李二嫂,潘氏早就算准了她们会传闲话。
果然,当天下午顾同兄弟回来时,这事已经传遍了洛宁县。邱氏关着门不肯见人,李红跪在院子里不停地磕头。
顾同虽没亲眼看见,可一看这情景,啥都明白了。潘氏哭哭啼啼的,说都是自己的错,把李红当成了贼,还惊动了街坊。顾同叹了口气,知道这事怪不得妻子。
顾林快十四岁了,啥都懂,母亲做出这等丑事,他觉得没脸见人,躲在房里不肯出来。
按当时的规矩,主母跟下人私通,报官是要受杖责的,可本家不报案,官府也不会管。顾同思前想后,硬着头皮去见邱氏,没骂也没怪,只是好言好语劝慰。可他越这样,邱氏越觉得无地自容。
顾同抽了李红几鞭子,把他赶了出去,对外只说“家里进了贼,花匠李红捉贼时被扯掉了衣服,受了惊吓,辞工走了”。
外人哪会信?但多数人念着顾家平时的好,不愿背后嚼舌根,只有那些长舌妇还在添油加醋地传。
顾林起初不肯再见母亲,后来在顾同的再三劝说下,才一起去安慰她。可外面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扎人,邱氏实在扛不住了。五天后的晚上,她给顾同和顾林留了封信,把金库钥匙放在信上,然后上吊自尽了。
为了顾全脸面,顾同对外说“母亲被贼人惊吓,旧病复发去世了”。跟上次一样,体谅顾家的人不再议论,长舌妇们却还在说。
处理完邱氏的后事,顾同把金库钥匙交给了潘氏,账本也由她管了。
这事对顾林打击最大,母亲做了丑事,又自尽了,他痛不欲生。顾同怕弟弟想不开,天天把他带在身边,可一上街,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顾林越来越瘦,眼窝都陷了进去。
顾同心疼弟弟,特意去陕州城郊开了家收皮货的小铺,让顾林去打理,还让福叔跟着照顾他。这哪是为了做生意?就是想让弟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清静几天,等过几年长大了,或许就能想开了。
顾林懂大哥的心思,也觉得在洛宁待不下去,没多久就带着福叔去了陕州。
婆婆没了,小叔子走了,自己拿到了金库钥匙,潘氏心里乐开了花,可表面上还得装出难过的样子,哄着顾同。
邓氏当初出这馊主意,说到底就是为了钱——儿子潘茂是账房,女儿管着顾家财务,还有比这更方便捞钱的吗?潘氏也明白,只要哥哥别太过分,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货行利润高,漏点就够娘家人富足了。
可她忘了,她和娘、哥都是贪财的人,三个贪鬼凑在一起,哪能长久?
邓氏和潘茂一条心,总嫌潘氏给的少;潘氏虽想帮娘家,可终究是顾家人,得为丈夫和儿子着想,不可能任由他们予取予求。
头两年还好,从第三年开始,矛盾就出来了。邓氏母子骂潘氏小气,潘氏怨娘和哥太贪,天天吵架。
顾同对此一无所知,他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盘算着再过两年,就把家产分成两半,自己和弟弟各一半,再给弟弟成个家,也算对得住爹娘和弟弟了。
顾林在陕州过得不错,没人背后议论,心情好了,生意也做得有声有色。顾同每两个月就去看他一次,兄弟俩喝喝酒,说说话,感情越来越深,跟着去的福叔看了,心里直乐。
潘氏和娘家的矛盾越来越深。这天,潘茂来报账,兄妹俩当着账房先生的面就吵了起来。
潘氏气得发抖:“大哥!你也太贪了!这么做账,我丈夫辛辛苦苦挣的钱,岂不是都给你填了窟窿?”
潘茂一脸无所谓:“妹妹,你们家富得流油,这点钱算啥?别这么吝啬。哥哥再做两年,就自己开铺子,到时候就不占你便宜了。”
潘氏不肯让步:“没你这么做事的!这两年你拿的还少吗?足够你们母子享半辈子福了,做人不能贪得无厌!”
潘茂眼睛一瞪:“要不是我和娘出主意,你能掌家?能独吞家产?逼急了我就跟妹夫说清楚,看你怎么办!”
这可真是引狼入室。潘氏没辙,只能吃哑巴亏,心里安慰自己:“算了,哥哥拿再多,也比将来分给弟弟一半强。”可她那贪财的性子哪忍得住?整天琢磨着怎么摆脱娘和哥。
就在潘氏心烦、邓氏母子偷偷得意时,一件小事让他们的阴谋彻底败露了。
不久后,李红偷偷去了潘家,找潘茂要钱。当初潘茂找他时,正是他娘病重缺钱的时候,潘茂说“顾家好面子,肯定不会报官,顾同心善,最多打你一顿”,他一咬牙就答应了。后来顾同没怎么为难他,他心里一直挺愧疚。
可前不久,他娘又病了,比上次还重,他去找潘茂借钱,没想到邓氏母子一分没给,还把他赶了出去。结果他娘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没了。
李红是个孝子,媳妇早逝,他一直没再娶,就守着娘过。现在娘没了,他啥都不在乎了,直接找到顾同,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全说了——他是被潘茂收买的,目的就是勾引邱氏,好让潘氏掌家。
顾同再善良,也忍不了这种事。妻子、岳母、大舅哥,这三人也太恶毒了!他当即写了状纸,把他们告到了县衙。
有李红作证,加上县衙的刑讯,邓氏、潘茂、潘氏很快就招了。知县气得拍了惊堂木,判邓氏和潘氏各杖打五十,游街三日;潘茂和李红各杖打八十,流放两年;还让顾同清点账目,潘家侵占的财产必须全部返还。
公堂上,顾同当场就休了潘氏,知县也支持他,亲自做了保人。
邓氏和潘氏游街三日,脸算是丢尽了。回家第二天,邓氏上吊了,潘氏服了毒。
李红和潘茂挨了八十板子,皮开肉绽。李红身子骨结实,熬完两年流放,去了别的地方重新生活。潘茂养尊处优惯了,被打残了,等流放期满回家,妻儿早就跑了,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
街坊邻居说起这事,都骂潘家人蛇蝎心肠,活该有这结局。也有人说邱氏可怜,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要是能守住本分,潘家人又怎能得手?
这事过后,顾同让弟弟回洛宁,可顾林还是放不下母亲的事,想继续在陕州住。顾同拗不过他,只好同意,还把家产分了一半给弟弟,在陕州给他置了宅子,帮他成了家。
弟弟成家一年后,顾同娶了个农家女子黄氏。黄氏温柔贤惠,话不多,却做得一手好饭菜,对顾同的儿子也视如己出。后来她又给顾同生了一儿三女,夫妻俩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多年后,顾同和顾林都老了,家业交给了儿孙。这时候顾林才带着媳妇回了洛宁,兄弟俩找了处安静的宅院住在一起,每天晒晒太阳,喝喝茶,安安稳稳地享受晚年。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原本幸福的家庭,就因为一个“贪”字,差点毁了。都说“好女旺三代,坏女毁一族”,潘氏贪财贪权,又碰上更贪的娘和哥,结局早已注定。邱氏虽是可怜人,可身处富家长辈之位,继子孝顺,亲子听话,却因为一时糊涂动了贪色之心,最终落得自尽的下场,也怨不得别人。
顾同重孝重情义,这样的人当家,家业自然兴旺,可他也有缺点——太容易相信人。明知潘茂贪财,还让他当账房,实在不算明智。
说到底,做人做事还是得守着一个“正”字,不然迟早要遭报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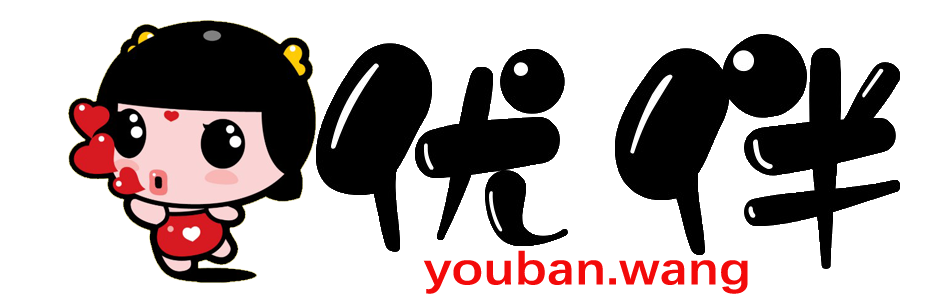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