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暮云镇的地方,镇西头有个魏记杂货铺,掌柜叫魏大通。这人做人守信,心地善良又厚道,人缘特别好,铺子生意也红火,在镇上算得上是小富之家。
魏大通的妻子姓胡,也是个心慈仁善的人,嫁过来后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刚出嫁没多久,儿子魏明还没成年,在学堂里读书。
离暮云镇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江。那年夏末,魏大通去县城进货回来,摆渡过江的时候,发现水里飘着一块大木板,一头趴着个中年男人,另一头是个孩子。
魏大通为人善良仗义,赶紧喊:“艄公师傅,快拿锚钩来,把木板拦下,救这两个人!”
艄公却说:“看那两人的样子,估计已经没气了,掌柜的就别费这个心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别废话了!”魏大通一边说着,一边自己去船尾拿竹竿。
艄公见他这么坚持,赶紧过来帮忙。两人合力把木板勾到船边,把那两个人救了上来,伸手一探,还有鼻息。
魏大通这才露出笑容。船靠岸后,魏大通在附近请了几个民夫,把货物和救上来的两人一起带回了家,请了郎中来看。
过了半个时辰,两个人醒了过来。中年男人叫居茂,是20里外胡家镇的货郎,在上游摆渡过江时不小心掉了下去。
那个孩子叫冯大,才10岁,是个乞丐,偷偷爬上船,结果也不幸落了水。
在魏家住了一夜,两人恢复了体力。居茂起身告辞,说改日一定登门重谢。
冯大是个乞丐,无家可归,魏大通可怜他,就把他留在铺子里做了小伙计。
三天后,居茂带着妻子赵氏来到魏家,还带来不少贵重的礼物,感谢魏大通的救命之恩。魏大通坚决不收礼物。
胡氏心地善良,就在镇上的饭馆点了些酒菜,招待居茂夫妇。
赵氏很会说话,拉着胡氏问这问那,还去前面的铺子转了一圈。
等丈夫去如厕时,赵氏跟上去小声说:“当家的,我看魏明那孩子挺好,比咱们女儿香菱大一岁,特别般配,要不结个亲家?”
居茂心里清楚,妻子有些贪财,肯定是看重了魏家的富贵。但他也挺喜欢魏明,再说魏大通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不肯收礼物,结个亲家也不错。
抱着这个念头,从厕所回来后,居茂就跟魏大通说了自己的想法。这种好事,魏大通夫妇自然不会反对。
就这样,两家结了亲。当时魏明11岁,香菱10岁,两家商量后,把婚事定在了8年后。可世间的事,变化无常,人的福祸也是如此。
四年后,魏大通借了一笔银子,在当地采购了一批绸缎,想运到府城去大赚一笔。谁知半路失火,绸缎全烧光了,血本无归。因为借银子时抵押了杂货铺,现在还不上钱,杂货铺就被收走了,魏家从此没落。
魏大通是个看得开的人,并没有被打垮。女儿女婿送来的钱,他都没收,又像当初刚成家时那样,挑起担子做起了货郎。
魏明已经15岁,还在读书,他也想分担家里的活儿,却被父母阻止了,让他安心读书,将来奔个好前程。
冯大现在14岁了,魏大通把他介绍到东街的饭馆做伙计,可冯大感激魏家的恩情,不愿意离开,也挑起担子,和东家一起做货郎。
魏大通夫妇非常感动,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
常言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赵氏当初撺掇丈夫和魏家结亲,图的就是魏家的钱财。现在魏家没落了,她心里就生了悔意,居茂多少也有些后悔,对魏大通的救命之恩也慢慢淡忘了。
转眼又过了3年,在魏大通和冯大的努力下,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当年魏明参加考试,没能中秀才,家人鼓励他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第二年的初秋,魏明和香菱的婚期到了。当地山川丘陵多,花轿马匹不好通行,所以流传下一个风俗:接新娘子过门都是用人背回来,背新娘的人被称为驮夫。
背着大活人走路,需要身强力壮的男子,一般是新郎的兄弟。如果没有兄弟,或者兄弟体弱,就雇请专门的驮夫。
冯大已经18岁,生得浓眉大眼,身强力壮,主动请缨来背少奶奶回家。
接亲那天,镇上的后生挑着聘礼,媒婆子也跟着,冯大背着个竹椅,一行人往胡家镇居茂家去。
两家的媒婆按照礼仪行事,一起去香菱的卧房,帮她梳妆打扮。魏家的媒婆见过香菱几次,见她又出落得漂亮了几分,心里很高兴,给她盖上红盖头,扶出门外。
冯大背过身蹲下,媒婆扶新娘坐上竹椅,几个吹鼓手奏起喜庆的乐曲,众人开始返程。
走到半路,香菱突然敲了敲竹椅,冯大停下脚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媒婆见她左手抓着罗裙,右手使劲攥着丝巾,不由一笑,心想香菱肯定是要去方便。
她让冯大蹲下,扶香菱下来,耳语几句后,明白了自己猜得没错,就让众人背过身去,扶香菱到旁边。
香菱微微撩起盖头,对媒婆说:“妈妈在这儿等着,我自己过去就行。”
媒婆说:“小姐,当心些,我在这儿等你。”说完,自己也背过身去。香菱走进林子,转到草丛后面。
没过多久,香菱从林中走出来,一行人继续上路。
冯大起身的时候,心里不由得犯嘀咕:咦?怎么新娘子好像重了一些?难道是我累了?
心里这么想着,脚步难免慢了下来。媒婆见他慢了,在后面催促:“冯大,走快点吧,回去晚了耽误了吉时,可不好。”
媒婆这么一说,打断了冯大的思路,他也没再多想,加快脚步赶起路来。
回到暮云镇,差不多也到了吉时,家里早已准备妥当。魏大通人缘好,镇上的人都来祝贺。
魏明穿着一身新郎装,很是英俊。一对新人按照礼仪拜高堂、拜天地,然后进入洞房,香菱坐在洞房里等候。魏明则留在外面,和亲朋友好喝酒。
大家都很高兴,把酒言欢,只有冯大坐在桌前发愣,眉头紧皱,像是有心事。
魏大通一直很看重冯大,也很呵护他,见他这副表情,上前问道:“怎么了,冯大?是不是累了?要是累了,就赶紧吃些东西,早点休息。”
“东家,我想跟您说点事儿,关于少奶奶……”冯大刚开口。
还没等他说完,有个中年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一把拉住魏大通说:“魏大哥,大喜的日子,兄弟们都等你过去喝酒呢,快来!”
魏大通笑着说:“放心,少不了你的酒。”他走出两步,转头对冯大说:“有事儿等明天再说,今晚先高高兴兴喝一顿,你也多喝几杯。”
“东家……”冯大还想说什么,可魏大通已经回到酒桌,和老友们欢快地聊了起来。
初更过半,宾客们才散去,魏明晃晃悠悠地进了洞房。魏大通喝得酩酊大醉,早已在房里睡熟了。胡氏在女客的劝说下也喝了几杯,不胜酒力,叮嘱冯大早些休息后,也回房了。
冯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一是新娘中途方便后,突然重了许多;二是新人拜天地时,他发现新娘好像高了一些,而且掩盖在罗裙下的脚,似乎也比接亲出门时大了不少。
自己虽然没见过新娘子的模样,但方便前后的差别,让他感觉不像同一个人。
冯大10岁时被魏家所救,说是收留做伙计,其实和养子没两样,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份恩情比天大,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东家受伤害。
想到这里,冯大披上衣服出门,悄悄来到洞房窗前,贴近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洞房内一片春色,隐约有嘤嘤的声音传出窗外。冯大虽然没成婚,但也听得出来,里面一片温馨。
难道真的是我累了?或许是太在意东家的安危了?不管怎么说,自己就在窗下守一夜,以防万一,等天亮了也就踏实了。
冯大抱着这个念头,坐在廊下,倚着墙壁守了一夜。
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传来呼唤声:“傻小子,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冯大迷迷糊糊睁开眼,见胡氏站在面前,此时东方已经发亮,应该过了五更天了。
“臭小子,年纪不大,学会听房了?跟我过来。”魏大通刚出门就看到这情景,把妻子和冯大叫到房里。
进屋后,魏大通笑着说:“你小子也该成婚了,过些日子,我帮你物色个好女子,省得你年轻气盛,在这儿听洞房。”
冯大脸上一红,支支吾吾地说:“东家,您误会了,我不是听洞房,我是……”
见他这样,胡氏在一旁说:“哎呀,你10岁就进了这个家门,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吞吞吐吐的做什么?”
冯大就把昨天的事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之所以不肯直说,是担心自己怀疑错了,那样就不好了。
听完冯大的话,魏大通夫妇也很惊讶。他们知道,冯大这孩子虽然没读过书,但做事谨慎,心思细腻,他的怀疑绝对不是无中生有,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魏大通想了想,说:“这事儿先到这儿,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几天再说。”
三人刚说完,魏明和香菱也起床了,按照规矩,二人过来给父母敬茶。
魏大通夫妇喝了媳妇茶,心里很高兴,但因为刚才冯大的话,不由得多看了香菱几眼。
当天晚上,魏大通对胡氏说:“上次见到香菱,还是她13岁的时候,虽说女大十八变,可这变化也太大了。我记得她的眼睛随居茂,可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她那两个哥哥一年前来过咱家,兄妹之间应该有几分相像,可她们兄妹差别很大,没有相似之处。难道……”
胡氏一边铺床一边说:“哎呀,心里有怀疑,才越看越不像。要不是冯大那番话,可能就越看越像了。若不是香菱,还能有谁?居茂家就这么一个女儿,别乱想了。这儿媳落落大方又勤快,不是挺好吗?”
“或许是我多心了,算了,不想了,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理。这几年多亏了冯大,咱们也有了些积蓄。杂货铺自从张掌柜接手后,生意不咋地,最近听说要转让,明天我就去找他压压价,盘回来。以我的本事,用不了三五年,就能重现当年的兴隆。”魏大通说完,歪过头睡了。
胡氏知道丈夫的能力,对此也很高兴,熄灯后也睡了。
到了第三天,按照习俗要回门,冯大担心少东家的安全,陪着他去了胡家镇。
女儿回门,居茂夫妇表现得很高兴,点了桌酒菜招待魏明和冯大。居茂家最近几年发了笔小财,居茂父子不再做货郎,在镇上开了家布庄,生意不错。
冯大心里还是有个坎,在居茂家时,很留意居家人对少奶奶的态度,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但他很谨慎,回家后也没说。
第二天晌午,冯大借故出去逛逛,其实是去了5里外的李家庄——接亲的媒婆李大娘就住在这个村子。李大娘年纪不小了,帮魏家办完婚事,就很少出门,在家养老。
李大娘性子爽朗,见冯大前来,笑着说:“大老远来找我,干嘛?难不成是想让我给你说亲?那可不行,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已经金盆洗手了。”
冯大笑着说:“不是,今天来是想问问大娘,我家少奶奶缠过脚吗?”
李大娘一愣,说:“奇怪,你问这个干嘛?自己不会看吗?”“好大娘,您就告诉我吧,求您了。”
见冯大一脸真诚,李媒婆说:“听说缠过,但时间不长,因为居茂家主母心疼女儿。不过你家少奶奶的脚,比普通农家女子小很多。”
“那我家少奶奶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嘴巴是大还是小?”冯大继续追问。
李大娘突然收住笑脸,说:“你小子有毛病吧?你在魏家天天能见到你家少奶奶,怎么跑来问我这些?你说老实话,不然我就再出一次门,告诉你东家去。”
见她这样,冯大支支吾吾地说:“大娘,我可以跟您说实话,但您要发誓,不能告诉别人。”
“好,我发誓,若说与别人,就让我肠穿肚烂下地狱,这总成了吧。”李大娘也是个好事的人,想知道内情,只能发毒誓。
冯大凑上去,小声嘀咕了几句。李大娘听完,惊道:“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有些奇怪。这样吧,不嫌累的话,你背我去一趟,我见过居香菱,一看便知。”
就这样,冯大又当了一次驮夫,背着李媒婆回了魏家。
当李大娘见到香菱后,事情揭开了真相——这个香菱竟是假的。
自从魏家没落后,居茂财运亨通,还开了布庄。富贵之后,他和妻子赵氏一样,对女儿的婚事生了悔意。可他爱面子,不愿做悔婚的事,为此心事重重。
大约一年前,府丞部的商人宋广来居茂家收债,无意间看到了香菱,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宋广30出头,家财万贯,妻子两年前病逝,还没续弦,想娶香菱做继室,给出的聘礼十分丰厚。
赵氏贪财,对丈夫说:“宋广家大业大,单是这些聘礼,我们10年都未必挣得到。要是女儿嫁给他,自然就是富家少奶奶,两个儿子也能跟着沾光,总比跟着魏家好。魏家已经没落,魏明也求不到功名,女儿过去不是受苦吗?”
居茂也是贪财之人,妻子的话说到了他心坎里。当年悔婚对名声不好,他不会做,但为了攀附富贵,绞尽脑汁想出一条计策。
接亲当天,不出居茂所料,魏家让李媒婆前来。李婆子认识女儿香菱,所以让女儿打扮成新娘,出门坐上竹椅。走到半路,香菱按照父母的叮嘱,假意去林中小解,其实密林深处,已经有两男一女等候——两个男子是居茂的儿子,那个女子名叫烟翠,是居茂大儿媳过门时带来的丫鬟。
等香菱进入密林,就用烟翠和她调换。因为新娘子一路都盖着红盖头,直到新郎进洞房才会揭开,中间不可能被发现。
等魏明和烟翠拜了天地,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就改不了了。而且居茂很了解魏大通,以他的敦厚性子,绝对不会上门讨要说法。这样既攀附了权贵,又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居茂算盘打得不错,没想到烟翠比香菱重一些,个子也高,而且没有缠足,再加上冯大警觉,发现了蹊跷,才揭开了真相。
真相大白,胡氏非常气愤,怒道:“居茂真是混账忘恩负义!我不怪他嫌贫爱富,可做出这等负义的事,太让人气愤了,这不是在羞辱我魏家吗?一定要去讨个说法!”
魏明的性格随父亲,再说这几天接触下来,他对烟翠这个妻子很是喜欢,也就没太在意。烟翠自觉愧疚,跪在公婆面前请罪。
果不出居茂所料,魏大通真是敦厚性子,他让儿子扶起儿媳烟翠,叹着气说:“嫌贫爱富,人皆有之,不必介怀。烟翠和明儿拜了堂,就是我魏家的媳妇,这事就算了。我们以后不与居茂家来往,这事儿也不必说与外人。我已经同张掌柜谈妥,杂货铺过几天就盘回来。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理,明儿好好读书,争取两年后考上功名。冯大,也别着急,我会找媒人给你说个媳妇。要不了几年,我们魏家肯定能重现辉煌。”
李媒婆被魏大通的话感动了,笑着说:“魏掌柜真是心善大度,我老婆子都不知道说啥了。这样吧,我重新出山,做最后一次媒人,给冯大找个好媳妇。”
他这话一出,几人都笑了。胡氏也是心善的人,刚才爆粗口是一时气愤,她拉过烟翠,柔声说:“闺女,别自责了,与你无关,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烟翠听婆婆这么说,喜极而泣。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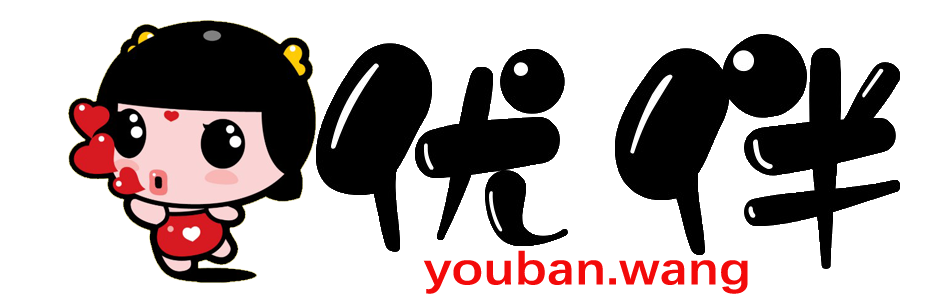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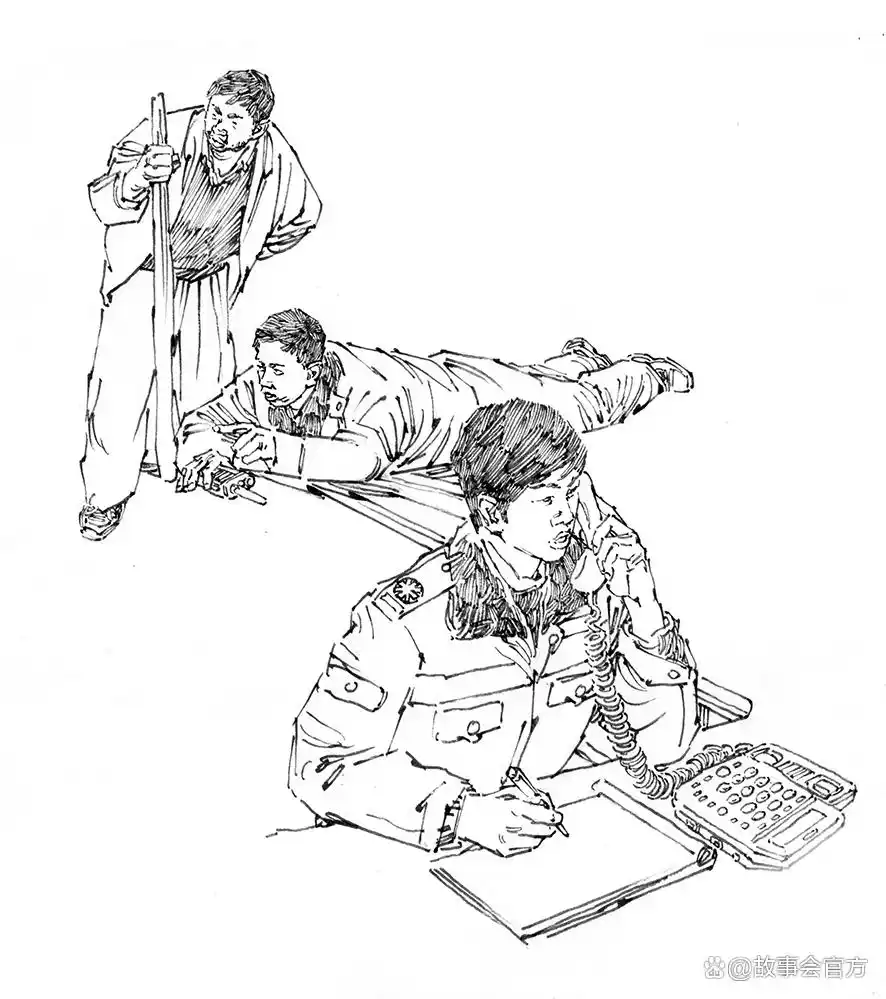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