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观音菩萨在紫竹林打坐,见人间炊烟袅袅如带,忽然动了凡心。她掐指一算,莲花渡口近日有场因果要了结,她摇身一变,成了个瞎眼老婆婆,挎着个篮子,里头装着些青翠的柳枝,慢慢悠悠就晃到了莲花渡口。
这莲花渡口的集市可热闹了,叫卖声、说笑声混在一块儿,直往人耳朵里钻。卖糖人的师傅正捏着个金鲤鱼,糖稀在他手里转着圈,亮晶晶的;挑着菜担的老汉扯开嗓子喊:“刚拔的萝卜,水灵得很哟!”观音刚走到胭脂铺跟前,就被一阵香粉味呛得咳嗽了两声。
这胭脂铺的老板娘钱二姑,是出了名的刁钻。她眼尖,瞅见个瞎眼老婆婆,眼珠“滴溜”一转,故意把一盒胭脂往地上一甩。“啪”的一声,嫣红的粉末洒了一地,混着尘土,成了难看的泥团。
“哎呀!”钱二姑的尖嗓子一下子就炸了,她几步冲过来,一把揪住老婆婆的袖子,指甲都快掐进布眼里了,“你个老瞎子,踩碎了我家祖传的胭脂!这可是值十两银子的好东西,不赔钱别想走!”
周围赶集的人一听,呼啦一下就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老婆婆叹了口气,声音慢悠悠的:“钱掌柜,我一个瞎老婆子,哪有银子赔呀?您说该咋办?”
钱二姑撇着嘴,上下打量她一番,一脸嫌弃:“看你这穷酸样,也拿不出银子。这样吧,算你运气好,用你那篮子里的柳枝,把我后院那三口大水缸挑干净。干不完,这些柳枝就归我抵债!”
老婆婆没法子,只好跟着钱二姑去了后院。那后院堆着半人高的柴火,三口大水缸并排戳着,缸底沉着厚厚的黑泥,水面上还漂着些死蚊子,看着就膈应人。老婆婆佝偻着腰,从篮子里抽出根细细的柳枝,蘸了水,一点点往缸外挑。
柳枝软乎乎的,挑不了多少水,每蘸一下,水珠就顺着枝条往下滴,把她的袖口都打湿了。日头正毒的时候,她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滴在缸沿上,溅起小小的水花。钱二姑倒好,搬了把竹椅坐在门口,一边嗑瓜子一边监工,时不时还撇着嘴催:“磨蹭啥呢?等会儿饭都凉了!”
老婆婆没应声,换了根粗点的柳枝接着挑。胳膊酸得像不是自己的,每抬一下都咯吱响,到后来,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就这么从日头高悬挑到月亮挂上树梢,最后一口缸才见了底。老婆婆扶着缸沿想直起身,后腰疼得钻心,差点没站稳。
钱二姑打着哈欠站起来,踢了踢旁边的水桶,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滚吧!”连一口水都没给。老婆婆又渴又饿,挎着空篮子,一步一晃地往河边挪,想喝点河水润润嗓子。
刚到河边,就听见“啪”的一声鞭子响。周扒皮正叉着腰站在船头,他那艘运货的乌篷船歪歪扭扭漂在水里,船底“咕嘟咕嘟”冒着水泡。“喂,那瞎婆子!”周扒皮用鞭子一指老婆婆的篮子,“你那破柳枝正好能堵我船底的漏缝,堵好了,赏你半碗粥!”
老婆婆叹了口气,答应了。她摸索着找到船底的裂缝,把剩下的柳枝一根根往冰冷的河水里塞。河水凉得刺骨,没一会儿,她的手指就冻得通红发僵,跟老树皮似的蜷着。
塞完了,周扒皮踢了踢船帮,从怀里掏出个纸包,“啪”地扔在泥地上。纸包散开,露出半块硬窝头,上面还沾着黑泥。“赏你的!”他说完,吆喝着船工开船,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婆婆饿得眼冒金星,捡起那半块窝头,踉踉跄跄走到下游的芦苇荡,靠着棵老柳树想歇口气。她实在太饿了,看见柳枝上冒出的嫩黄芽儿,忍不住想折两根润润干裂的嘴唇。
“婆婆,别折!”一个清脆的声音喊起来。阿水拎着鱼桶跑过来,他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泥点。看清老婆婆手里的脏窝头,还有她那疲惫的样子,阿水赶紧摆手:“几根柳芽算啥?您要是饿了……”他话没说完,转身就往不远处的破茅棚跑,没一会儿,端着个豁口粗瓷碗回来了,碗里是半块热乎的鱼饼,还冒着热气。
“这是我娘早上烙的,还有点余温呢。”阿水把碗递过去,又从怀里掏出个小竹筒,倒出些清水,“您慢点吃,别噎着。”
老婆婆接过碗,鱼饼的香味混着淡淡的鱼腥气,闻着就暖心。她狼吞虎咽吃完,对着阿水的方向深深作了个揖:“小哥心善,定有大福报啊。”
话音刚落,老婆婆身边忽然腾起白雾,裹着淡淡的莲香。阿水揉了揉眼,白雾散了,老婆婆没影了,只有一截青翠的柳枝落在他脚边,枝条上还挂着片鲜嫩的柳叶。
第二天,莲花渡口炸开了锅。钱二姑的胭脂铺里,所有的胭脂水粉一夜之间全黑了,还长了绿毛,腥臭味飘出半条街,客人跑了个精光。周扒皮的船刚划到河中间,堵船缝的柳枝不知咋的全漂了起来,船底的裂缝更大了,“哗啦”一下就沉了,一船货物全泡了汤。
可阿水家不一样。他早上推开茅棚门,就瞅见门口停着艘崭新的渔船,船板油光锃亮。昨天那截柳枝,变成了顶精巧的金柳帽,戴在头上凉丝丝的。阿水划着新船去打鱼,渔网刚撒下去就沉甸甸的,拉上来一看,满网都是活蹦乱跳的大鲤鱼。
街坊们都说,这是那瞎婆婆显灵了。其实他们不知道,那哪是普通的瞎婆婆啊,是南海紫竹林来的观音菩萨,特意来人间看看善恶,给心善的人指条亮堂路呢。
你看,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人在做,天在看,行善积德才是安身立命的真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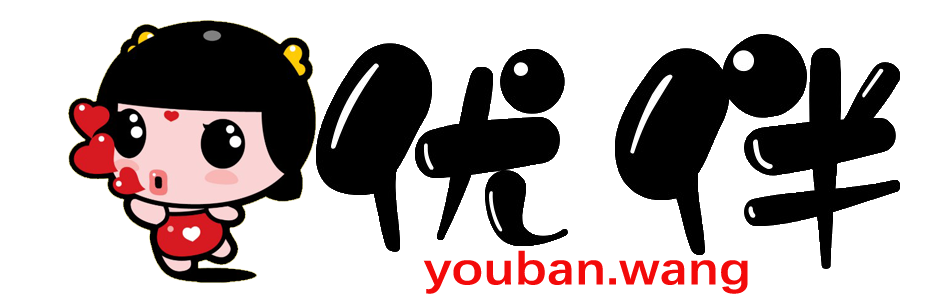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