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啊,有个可怜的小乞丐。打小起就没见过爹娘,街坊邻里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叫啥。大伙儿看他总在街头讨饭,顺口就叫他“小叫花”。
小叫花这孩子,日子过得苦极了。白天揣着个破碗,在苏州府的大街小巷里转悠,见着谁都得陪着笑脸,“大爷行行好”“奶奶给口饭”地求着。运气好的时候,能讨着半个馒头或是一碗剩粥;运气差了,可能一整天都填不饱肚子,还得挨些白眼和呵斥。
到了晚上,街面上的铺子都关了门,冷风一吹,小叫花就缩着脖子往城隍庙走。那庙虽说不算气派,可走廊下好歹能遮风挡雨。他就把墙角那堆别人不要的干草拢一拢,当成褥子,再把破棉袄往身上一裹,就算是歇脚的地方了。
夜里躺在干草上,总能听见庙里的动静。香客们白天来烧香,有提着篮子的妇人,有牵着孩子的男人,嘴里念叨着“求城隍爷保佑孩子平安”“求城隍奶奶赐个好姻缘”。小叫花竖着耳朵听,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他瞅着那些被爹娘护在怀里的孩子,手里攥着糖葫芦,或是新做的布偶,笑得咯咯响,心里头像被针扎似的疼——为啥别人都有爹娘疼,就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呢?
有天夜里,他盯着神龛上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塑像,忽然心里一动。那城隍爷穿着红袍,脸上带着慈眉善目,城隍奶奶端坐在旁边,手里还捏着个小娃娃,看着就亲。小叫花爬起来,对着塑像“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小声说:“城隍爷,城隍奶奶,我没爹没娘,你们就当我的爹娘吧。我以后天天给你们烧香,给你们磕头。”
从那以后,小叫花讨饭更上心了。他把每天讨来的钱仔细数一遍,哪怕只有几个铜板,也得攒着。等攒够了买香的钱,就跑到庙里的香烛铺,选一根最细的香——贵的他买不起,可这细香,也是他的一片心。
每天傍晚,香客渐渐散了,小叫花就捧着那炷香,恭恭敬敬地走到神龛前。他先把香在蜡烛上点着,看着火苗舔着香头,冒出淡淡的青烟,再双手捧着香,举过头顶,对着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塑像拜三拜。拜完了,才小心翼翼地把香插进香炉里。香烧着的时候,他就蹲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说心里话:“爹娘,今天我讨着了半个肉包子,可香了,我留了一小块给你们。”“今天有个大婶给了我件旧棉袄,穿上不冷了,你们也暖暖和和的。”
就这么着,春去秋来,整整三年。小叫花每天都来烧香,香炉里的香灰堆了一层又一层,他的破棉袄换了一件又一件,可对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心意,一点儿没减。
这天晚上,小叫花累了一天,蜷缩在走廊的干草堆里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他听见神龛那边传来说话声,细细软软的,像是个老太太的声音。
“老头子,你瞅瞅,走廊那孩子,给咱们烧了三年香了。”是城隍奶奶的声音,带着点儿心疼,“这孩子太可怜了,天天吃不饱穿不暖的,能不能让他发点财,过几天好日子?”
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是城隍爷:“这孩子是心善,也虔诚,可他命不好啊。我让人查过了,他阳寿不长,明年十月初八就是死期。怕是没福气发财了。”
“那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城隍奶奶急了,声音都拔高了些,“他把咱们当亲爹娘待,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没了吧?”
“天命难违啊。”城隍爷又叹了口气,“每个人的命数都是定好的,我也改不了。”
后面的话,小叫花没听清。他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透了,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板。他抱着膝盖,把脸埋在破棉袄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他想,自己这辈子,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没被人疼过一天。好不容易认了个“爹娘”,还没享过一天福,就要死了。既然是命里注定的,那哭也没用。不如趁着剩下的一年,到外面走走看看。苏州府他待了这么久,别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有城隍庙?是不是也有像他一样讨饭的孩子?
天亮前,小叫花抹了把眼泪,最后看了一眼神龛上的城隍爷和城隍奶奶,对着他们磕了个头:“爹娘,我走了。等我到了那边,再给你们烧香。”说完,他揣着剩下的几个铜板,趁着夜色,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苏州府。
他一路往南走,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在破庙里或是屋檐下。有时候遇上好心的店家,能给碗热汤;有时候遇上恶狗,得抱着头跑半天。可他不觉得苦,心里头有个念想——得多看看这世界。
几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他走到了杭州城外。城门早就关了,城墙上的灯笼晃悠悠的,照着守门的兵丁来回走动。小叫花没法进城,只好往城郊走。远远看见一片坟地,坟头前还有个供桌,看着还算干净。他走过去,把供桌上的灰尘擦了擦,就蜷缩在供桌底下,打算对付一晚。
刚睡着没多久,就听见坟地那头传来说话声,一粗一细,像是两个人在聊天。
“哎,你听说了吗?杭州知府家的小姐病了,都快不行了。”是个粗嗓门,听着像个壮汉。
“怎么没听说?”另一个声音尖细些,带着点笑,“知府都快把杭州城翻过来了,请了多少大夫,都治不好。现在满城贴告示,说谁能治好小姐的病,赏黄金百两呢。”
“百两黄金?”粗嗓门的人惊了一下,“那可是能买好几套房的钱!不过那小姐的病就那么难治?”
“也不是难治,”尖细嗓门的人压低了声音,“是没找对法子。我跟你说,知府家后花园的荷花池里,养着一只白鹅,都活了一百年了,早就成精了。只要从它头上拔三根硬毛,煎成汤给小姐喝,保管药到病除。”
“真的假的?”
“我还能骗你?不过啊,咱们是阴间的差役,受不得人间的香火,那黄金跟咱们没关系。”
小叫花在供桌底下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咯噔”一下。百两黄金?他没见过黄金,可知道那是好东西。不过他更记着那句“拔三根鹅毛煎汤能治病”。他想,要是能治好小姐的病,就算不要黄金,能讨碗饱饭也行啊。
第二天一早,城门一开,小叫花就随着人群进了城。城里可比苏州府热闹多了,街上卖什么的都有,糖画、面人、还有香喷喷的桂花糕。他顺着路人的指引,找到了知府衙门。衙门门口果然贴着告示,红纸上写着黑字,说谁能治好小姐的病,赏黄金百两,还能让小姐认他当干爹干娘。
小叫花挤到告示前,看了半天,鼓起勇气对守门的衙役说:“大哥,我能治好小姐的病。”
衙役上下打量他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还有泥,忍不住笑了:“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儿捣乱,快走开!”
“我没捣乱,”小叫花急了,“我知道怎么治。”
正吵着,衙门里走出个管家模样的人,问清了缘由,皱着眉说:“既然你说能治,那就跟我进来吧。要是治不好,可有你好受的。”
小叫花跟着管家进了衙门,穿过几重院子,来到后堂。知府正坐在椅子上叹气,见进来个小乞丐,眉头皱得更紧了:“你能治病?”
“能。”小叫花点点头,“大人,您家后花园是不是有个荷花池?池里是不是有只大白鹅?”
知府一愣:“是啊,那鹅是我家传下来的,养了好些年了。你问这个干啥?”
“那鹅成精了,”小叫花说,“只要从它头上拔三根硬毛,煎成汤给小姐喝,病就好了。”
知府半信半疑,可女儿的病实在拖不起了,只好让人去后花园抓鹅。没多久,下人就捧着三根雪白的鹅毛进来了,说那鹅确实神气得很,抓的时候还扑腾着翅膀叫了半天。
知府让人赶紧把鹅毛煎成汤,端到小姐房里。没过半个时辰,就听见房里传来丫鬟的叫声:“小姐醒了!小姐说饿了!”
知府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进房里,见女儿果然坐了起来,脸色也红润了些,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转身走到小叫花面前,对着他作了个揖:“小兄弟,大恩不言谢!你要什么赏赐?黄金百两,还是别的?”
小叫花摇摇头:“我不要黄金。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明年十月初八就没命了,拿着黄金也没用。”
知府一愣:“小兄弟,你这话啥意思?”
小叫花就把在苏州府城隍庙听到的话说了一遍。知府听了,眼圈也红了:“好孩子,你别这么说。我就一个女儿,要是不嫌弃,你就当我的干儿子吧。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小叫花对着知府磕了个头:“干爹!”
知府高兴极了,留他在府里住,还给了他新衣裳穿。可小叫花住了几天就想走:“干爹,我还想再走走。明年十月初八,您要是有空,就去苏州府城隍庙,给我收个尸,我就知足了。”
知府拗不过他,只好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又派了个下人送他出城。临走时,知府拉着他的手,眼圈红红的:“儿子,到时候干爹一定去。”
小叫花揣着银子,继续往前走。这银子他舍不得花,总觉得得用在正经地方。
又走了些日子,他到了宁波城外。这天下午,他正沿着护城河走,忽然听见前面传来哭声,撕心裂肺的,像是有人遇到了天大的难处。
他跑过去一看,是个中年妇女,跪在河边,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泪。她一边哭,一边往河里爬,嘴里还念叨着:“我对不起你啊,当家的!我没照顾好孩子……”
小叫花赶紧冲过去,一把拉住她:“大婶,你别寻短见啊!有啥难处,说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决!”
妇人被拉住了,瘫坐在地上,哭着说:“我当家的是个秀才,进京赶考去了,家里就我和两个孩子。昨天夜里,两个孩子突然发起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还胡话。我想请大夫,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眼看着孩子就快不行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小叫花听着,心里酸溜溜的。他摸了摸怀里的银子,那沉甸甸的感觉还在。他把银子掏出来,塞到妇人手里:“大婶,这银子你拿着,快请大夫给孩子看病!钱没了可以再讨,孩子的命不能等!”
妇女看着手里的银子,足有一百两,吓得赶紧往回推:“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拿着!”小叫花把银子往她怀里一塞,“快去!”
妇人这才反应过来,对着小叫花“咚咚”磕了两个头,爬起来就往城里跑。小叫花也跟了上去,帮着她找大夫,抓药,又跑回妇人家,帮着烧火煎药。
那两间茅草房很小,屋里黑乎乎的,两个孩子躺在一张小床上,脸蛋烧得通红,嘴里还哼哼着。小叫花守在床边,一会儿给孩子擦汗,一会儿摸摸他们的额头,比自己生病还着急。
就这么忙了三天,两个孩子的烧终于退了,能睁开眼睛叫“娘”了。妇人高兴得直掉泪,拉着小叫花的手说:“好孩子,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你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下,我给你做新衣裳,给你做你爱吃的!”
小叫花摇摇头:“大婶,我活不了多久了,明年十月初八就到期了。我从小没娘,您要是不嫌弃,就当我的干娘吧。到了那天,您要是有空,就去苏州府城隍庙,给我收个尸,我就心满意足了。”
妇人抱着小叫花,哭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又过了些日子,小叫花辞别了干娘,继续往前走。他一路走,一路帮人——帮挑担子的老汉扶一把,帮看铺子的大娘哄孩子,把讨来的干粮分给比他还小的乞丐。他觉得,能多帮一个人,这日子就没白过。
不知不觉,就到了秋天。小叫花算算日子,也该回去了。他一路往北,又回到了苏州府城隍庙。
还是那条走廊,还是那堆干草。他把干草拢了拢,躺上去,觉得格外亲切。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塑像还在神龛上,看着就像在对他笑。他又去买了炷香,点上,插在香炉里,笑着说:“爹娘,我回来了。”
十月初七那天,天阴沉沉的,下起了小雨。小叫花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头也晕乎乎的,像是有千斤重。他知道,时候快到了。
初八早上,雨还没停。小叫花躺在干草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迷迷糊糊中,听见庙外传来一阵喧闹声,还有马蹄声和车轮声。
“让让!都让让!”有人在喊。
接着,一个穿着官服的人冲进了庙,后面还跟着几个随从,抬着一口棺材。那人一眼就看到了走廊下的小叫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放声大哭:“干儿子!干爹来晚了!”
小叫花勉强睁开眼,认出这人是宁波那位妇人的丈夫——他身上的官服,看着就气派。后来他才知道,这位秀才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衣锦还乡了。回家后听妻子说了小叫花的事,立刻带着棺材赶来了。
状元正抱着小叫花哭呢,庙外又传来一阵马蹄声,比刚才的还急。紧接着,一个穿着知府官服的人也冲了进来,身后也跟着人,抬着一口更气派的棺材。
“儿子!我的儿子!”杭州知府一边喊,一边往走廊跑。
看到状元抱着小叫花,知府急了:“你放开!这是我干儿子!”
状元也不让:“他是我干儿子!是他救了我妻儿的命!”
“他先认的我!”知府以前是武将出身,力气大,一把就想把小叫花抢过来。
“我是状元!你得听我的!”状元也不含糊,紧紧抱着小叫花的腿。
两人你拉我扯,吵得不可开交。随从们想劝,又不敢上前——一个是知府,一个是状元,都是惹不起的大人物。
就在这时,城隍庙门口闪过一道黑影,一个小鬼拿着铁链,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他是来勾魂的,按阎王的吩咐,这会儿该把小叫花的魂勾走了。可他刚想进门,就看见小叫花身上罩着一团红光,暖暖的,把他挡在了外面。小鬼挠挠头,没办法,只好一溜烟跑回了地府,向阎王禀报。
阎王听说勾不了魂,亲自来了。他站在庙门口一看,也愣了——那团红光是文曲星和武曲星的气数,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前武将出身的知府,两人都把小叫花当亲儿子护着,那气场,他也不敢硬闯啊。
正没办法呢,看见城隍爷站在神龛旁边,捋着胡子笑。阎王走过去,拉着城隍爷问:“老城隍,这到底咋回事?这小叫花的阳寿今天就该到了,怎么被文曲星和武曲星护着?”
城隍爷笑着说:“阎王你有所不知。这孩子虽说命薄,可心善啊。他自己讨饭,还把银子给了状元的妻儿,救了两条人命;又帮知府救了女儿。这是积了大功德啊。依我看,不如给他改改命,也显得咱们地府有情有义。”
阎王想了想,觉得有理。他掏出生死簿,翻开一看,找到小叫花的名字,拿起笔,在阳寿那栏添了“六十年”。写完了,对城隍爷说:“行,就依你。这孩子,该有好报。”
说也奇怪,阎王刚改完生死簿,小叫花忽然咳嗽了一声,眼睛慢慢睁开了。他看着抱着他的知府和状元,还有旁边的棺材,懵了:“干爹,你们咋来了?我还没死呢……”
知府和状元一看他醒了,都愣住了,接着是狂喜。两人抱着小叫花,一个哭一个笑,眼泪鼻涕蹭了他一身。
后来,小叫花就在杭州知府家住了下来。知府请了先生教他读书,他也争气,没多久就识了不少字。过了几年,他长大了,一表人才,知府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宁波的状元夫妇也常来探望,把他当亲儿子疼。
小叫花活了整整六十年,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而且,每年的十月初八,他都会带着妻儿,提着最好的香,去苏州府城隍庙。对着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塑像,他总会说:“爹娘,你们看,我过得很好。这福气,是你们给的,也是我自己挣来的。”
香炉里的香,一年又一年地烧着,那烟飘啊飘,像是在说:善良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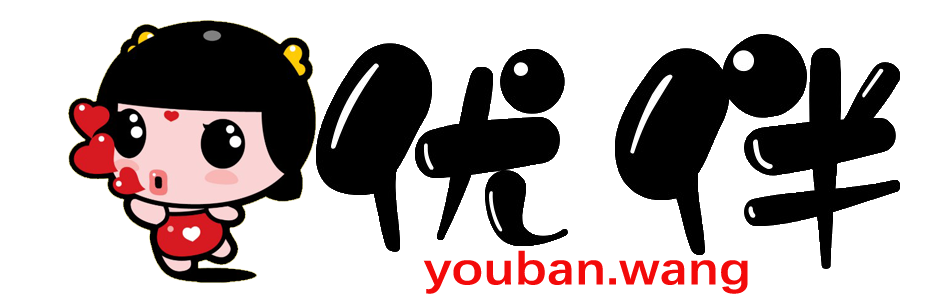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