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初, 未竣工的维尼纶厂。
厂房之间的空地上, 横七竖八地堆积着钢筋、木料; 凛冽的寒风中,
水泥袋的碎纸片漫天飞舞。维尼纶厂建厂指挥部的成员们正在陪同省
轻工局的几位领导视察着工地。
“ 三千万, 一个子儿也压缩不下去了? 成了钢性的了? ” 说这话的
是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 他那扫视着众人的似乎是狡黯的目光里
隐隐含着审视, 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 额上的皱坟特别深刻, 脸上的线条
象岩石裂缝般粗犷刚劲, 他以惯有的诙谐口气说着, 明显地流露出不满。
这位刚刚官复原职的丁局长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文化革命前, 他以果断执着在全省闻名, 曾有过许多美传。
这次他到维尼纶厂是来审查追加预算的。
维尼纶广是个建设十年还未竣工的“ 胡子工程” 了! 今年, 总算提出了一年竣工的计划。但建厂联合指挥部—— 这是由维尼纶厂( 通称甲方) 和负责施工的省建公司九处( 通称乙方) 联合组成— 却又同时提出了一个需要追加投资三千万元的申请报告。要知道, 维尼纶厂从最初的总概算五千万元, 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
地因为超支而追加投资, 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元了! 一个总概算才五千万元的项目, 要花三千万元来扫尾竣工, 无论如何是太不象话了! 他知道, 压缩投资是当今最难的事情。
连计委、建委、国家都没办法, 人人都说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状戈但他就是要在这上头试一试, 冲一冲这个谁也不敢碰的“ 现状” ! 他觉得,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 维尼纶厂的党委书记、联合指挥部的总指挥张安邦是他六五年亲自在一个纺织厂培养和提拔的千部。他了解他, 相信他会配合这次审查工作的。
但是, 事情并不象他预料的那样。十多年没接触, 张安邦变得陌生、不可捉摸了。
虽然他表面上对老上级显出一种特有的亲热、坦然, 但是在客气、尊敬中 总好象隔着层什么东西。在张安邦的安排下, 几天来对追加预算的审查, 也好象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云雾。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精确, 丝毫看不出漫天要价的迹象。要账目, 有摞两尺高的“ 预算书” 、“ 计算书” 送来, 数以千页的表格里填满了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数万个数字; 要听取意见, 指挥部甲乙两方都做了详细汇报; 好象三千方元无可非议, 只有拍板了!可是, 敷衍的客套, 官样的文章, 却使丁猛愈来愈愤懑!他始终感到有人张开了一张网, 罩住了一切, 使他根本看不到实情! 是谁张的网呢? 张安邦? 丁猛还不能断定。
“ 我们己经是一压再压, 没有一点弹性了!”
一摊双手答话的正是张安邦, 这位厂党委书记有着一张长圆的胖脸, 光润润的, 没有皱折, 没有棱角, 象团揉光的白面, 眉毛细淡, 眼睛漂亮而有神。
他的嗓门, 即使是这样随便说话也十分洪亮。话语里, 带有一种对老上级才有的亲近和诉苦的口吻。他说完又笑了笑, 很亲切地看了看左右。簇拥着他的部下们用迎合的点头和微笑呼应着。
“ 这是什么? ” 丁猛指着一座象是临时搭的烂仓库模样的建筑间。
“ 这是临时食堂。” 张安邦从容地回答。他指着旁边被水泥、机器堆满大厅的原来的食堂说:
“ 正式食堂做了临时仓库—— 因为仓库不够用—— 所以又盖个临时食堂, 职工吃饭总不能露天。” 说着他们已经走入了“ 临时食堂” 的大厅, 仰面是席片的棚顶, 低头是烂砖的地面, 墙上窗户没框, 横七竖八的木条钉住的塑料薄膜被风刮得
呼塌塌作响, 确实是一副“ 临时” 样。轻工局基建处的一位处长点头证实道: “ 盖临时食堂, 他们有过申请报告。”
丁猛打量了一圈大厅, 哼了一声说: “ 好一个临时食堂!……临时设施, 为什么搞水泥砂浆砌墙? 为什么还搞圈梁? … … 怕以后拆除起来太方便? 嗯—— ? ” 丁猛上上下下指划着, 两眼冒火地说, “ 这样大的面积, 大门大窗的设计, 看, 这儿, 连以后隔墙的基础都搞好了! 这是临时食堂? “ 一这是个大型俱乐部! 变一下就成
了! … … 搞假预算, 搞计划外项目! 犯法! ” 人群中一片寂静和窘怵, 大家都被意外的质问震慑住了。谁也没想到丁局长这样内行。问题严重了!
张安邦略含不满地扫视了一下大家, 转向丁猛, 坦然地笑了笑, 颇有些感叹地说: “ 没办法啊, 丁局长! 这都是前几年的极左路线逼出来的! 什么‘先生产, 后生活’! 谁敢公开搞个俱乐部啊!哪儿也不会批!… … 厂里尽是年轻工人, 总应该关心职工文化生活! ” 张安邦委婉而理直气壮的解释, 顿时扭转了气氛。大家都舒了口气, 暗暗佩服自己的总指挥。现在, 看来是轮到丁猛进退两难, 不好回答了!
“ 你还是有功罗? ” 丁猛看着张安邦讽刺道:
“ 现在是七九年了, 知道吗? … … 为什么还弄虚作假? ” 看到张安邦还要张嘴解释什么, 他一伸手打断说:
“ 你先写个检查——搞假临时食堂—— 准备接受处理!”
大家全怔住了!
“ … … 然后, 再打个报告— 申请盖俱乐部, 送局里批。”
这样的两条决定, 象云烟中划过一道闪电, 人们知晓了这位丁局长的份量! “ 总指挥没有是非原则!……其他同志呢? 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揭发、反映问题? ” 丁猛批评、质问的目光扫视着指挥部的成员们。没有一个人吭声。一堵沉默的墙!在伸手向国家多要钱上, 在“ 为集体的利益” 这面旗帜下, 一个企业的干部
往往是团结一致的。合情又合理, 谁也犯不着触犯众利, 谁也在里面多少有一份, 谁也要在本单位站住脚。这是现在很普遍的现状! 这个现状几天来嘲弄和激怒着丁猛。现在, 人们都在他的目光下垂着眼。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维尼纶厂
基建安装办公室主任白莎, 这位中年女技术员只是掠了一下额头从蓝色围巾下露出的一绺短发, 很快地睨了一眼丁猛, 照旧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别处。
“ 白莎同志, 你负责搞预算, 怎么也不坚持原则呢? ” 丁猛的目光移向她, 直率地批评道。白莎苍自清秀的脸上, 一下子泛起了温怒的红晕, 眼里射出冷冷的敌意。
“ 丁局长, 这事情完全应该我负责。” 张安邦站出来说话了, 态度十分诚恳, “ 同志们都是辛辛苦苦做具体工作的! 这几年, 都很不容易!错误, 完全在我。确实不能怪同志们。临时食堂这件事, 和三千万也没关系… … ”
“ 没关系? 你负责? 等着吧, 有你的责任负!” 丁猛斜睨了一眼张安邦, 心里说。张安邦在“ 临时食堂” 上玩的花样, 更使丁猛断定三千万有问题!他又看着白莎问: “ 白莎, 你对三千万的最后意见呢了”
“ 三千万, 这确实是维尼纶厂竣工最起码的数字了! —— 这意见我们都是一致的! ” 张安邦接过话头, 以老下级的身份带笑说, 他极力想缓和一下气氛。
“ 这个安邦真是怪了! ” 丁猛严厉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 怎么就一言堂了呢!白莎的脑袋不在她肩上?”
张安邦笑了笑, 一副甘愿接受丁猛任何批评的表情。
“ 白莎, 谈你的最后意见吧, 可不能光当头头儿的附庸! ” 丁猛说。
“ 当附庸? 我还没学过!’ 白莎带着刺, 冷冷地答道。了猛的话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这位兰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女技术员, 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在她眼里, 任何事情上的认真都是没必要的; 只要不触及她, 三千万就三千万吧!她参与了预算编制, 但从来都觉得与她无关。她不过是在厂里顺潮流而动, 干她的八小时而已。“ 白莎, 你态度冷静一些, ” 张安邦爱护地责 备道, “ 丁局长是让你谈对三千万的意见!”
“ 我没什么意见。” 白莎依然冷着脸, “ 三千万大概够了吧! ” 她看也不看丁猛, 甩了一下围巾, 扭过身去, 不说话了。
“ 大概? 这是搞经济工作的人说的话?”丁猛冒火了, 目光象剑一样在人群中扫动着, 连腮帮子都搐动起来。人群却仍然只有沉默。面对沉默的人群, 丁猛发觉自己应该冷静, 发火—— 那不过是软弱无力的表现, 他要打破罩住实情的这张网! 他顿时想到了那个难得的人物, 他睥睨了一眼张安邦, 威严地说:
“ 既然这样, 我要请个专家来查你们!……钱——维——
丛—— ! 听说过吗? ”
白莎不禁转过头, 眼睛里闪过一瞬的惊讶。 张安邦没料到丁猛还要来这么一下, 他爽朗地点了点头: “ 那当然好! 那就更可靠了! ” 脸上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他不知道钱维丛是什么人。他相信, 就是再内行的人, 也难从浩如烟海
的数字中, 几天内看出问题来。
“ 你们最好是自己先减码!……查住了, 可要当心!” 丁猛说。
二
当天下午, 白莎来到张安邦家。
“ 预算该重做就重做做吧!… … 钱工程师来, 这些账可经不住他查! ” 她很淡然地说道。
“ 哪有那么严重!” 张安邦毫不在乎地笑着摇了摇头。中午, 他已摸清了: 钱维丛是轻工局一个搞设计的普通工程师, 他的几子, 叫钱小博, 就在维尼纶厂当工人。
“ 信不信吧! 他过去是全国有名的预算专家! ”
张安邦疑惑了一下, 他既不知道钱维丛是预算专家, 也不知道所谓预算专家有多大份量, 为了掩饰自己的疑惑, 他反而很有气派地哈哈一笑, 用惯常对部下的和蔼的玩笑口吻说: “ 害怕罗? 为工作, 怕什么! ”
“ 我怕什么!’ 白莎恼了, 眼睛射出尖刻的目光, “ 我只觉得犯不着出事, 没必要! ” 说完, 一扭身走了。
看着白莎苗条的背影消失在门外, 张安邦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采取对策! … … 但是, 他却坐在沙发上恍惚了几秒钟。
他一刹那又想起上午视察完工地后, 丁猛对自己个别谈话中的批评, 是那样地中肯, 那样地坦率, 使张安邦真有些感动。
当时, 在丁猛既严肃又和蔼的目光下, 他也曾对“ 三千万” 产生过犹豫… …
这时, 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 是物资局来催间招工指标的。张安邦曾答应帮助弄几个招工指标, 把物资局几位局长的子女安排到省建公司— 而这又是和“ 三千万” 有关的。物资局里的人出的气都是粗的, 张安邦一连答应了几个“ 行!”
一个电话, 使他立刻看清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 看到了“ 三千万” 后面隐现的许多局长、部长们的脸。电话一挂, 他就恢复了毫不含糊的决
心——他必须弄到召三干万”
虽然, 他绝不会把其中哪拍一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他却必须把这“ 三千万” 搞到手。否则, 他在现实生活中会根本站不住脚的! 就说在厂里, 那些副书记、副厂长们要往一家一院的高标准平房; 行政科科长要盖一个由他支配的高级招待
所; 医院院长要让厂医院楼再加高一层, 为的是要更宽敞舒适的院长办公室… … 这各种各样的人物, 在维尼纶厂领导权的巩固过程中都给他上下出过力, 他们的要求都得给予满足!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他去争取“ 三千万” , 而绝不能有失众望,
造成众叛亲离!更广泛些说, 他要“ 三千万” 的目的远远不仅这一点。
一个钱多、物资多、汽车多、关系多的大厂书记, 加上足够的权谋机智, 在社会上就有许多无形的权力。而这无形的权力, 对于爱财的, 可以使家里沙发、电视机、电冰箱应有尽有; 对于他这样爱权的, 则有了向上进取的坚实基地。当然, 他也并不是天生爱权的。文化革命一开始, 他这个只当过一年副厂长的“ 当权派”
也住过几天牛棚, 那时, 他最后悔的是自己为什么当了副厂长。
但是, 经过一番表态、站队、反戈一击, 他也投入了急风暴雨。很快, 他领悟了
“ 政治” 的奥妙, 看到了“ 政治” 的天地。在急流旋涡中几经沉浮, 他埋葬了一个灵魂, 又膨胀了另一个灵魂, 他终于被造就了! 他虽然在十几年政治生活中饱尝了甜头和辛酸, 不那么急于求成了, 但还保持着政治上锲而不舍的意志。目前这个“ 三
千万” , 在厂内、厂外包含着他和许多方面利益的结合。远的不说, 在预算中不给省建公司算得宽点, 就搞不到招工指标, 那么物资局头头们的子女就没法安排。而不这样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 他又怎么能日益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系呢? 他
还想到了从物资上控制周围几个县, 想到了把家属在厂里工作的那些地委领导干部们都请到厂里来住高标准的平房。总之, 他深知这些年来的当官“ 诀窍” : “不把广泛的社会关系搞好, 是无法进取的! 现在是关系错综复杂的年头, 不一定是顶
头上司, 也许是哪一个不被注意的小人物, 往某一条线上递一句话, 就能决定你的升迁。在维尼纶厂, 一切和上层有联系的干部、工人, 他都要摸底。他的一个重要“ 工作” , 就是调看档案。哪怕你是个学徒工, 只要你的父母或者三姑六舅九姨
子中有一个硬牌人物, 就一定要弄清、记住, 在需要的时候, 用适当的“ 照顾” , 把你, 因而也把你的“ 背景” 织入他的网中。现在, 他就要用这张网来争取“ 三千万了” !
下班前, 他给钱维丛的儿子所在车间打了电话, 让他们通知钱小博晚上来他家里; 他告诉车间, 最近不要分派钱小博在班上的工作了, 厂党委另有任务交给他。
三
丁猛已经感受到了张安邦活动的包围。厂里的一些负责人和自己接触时无不从各个不同角度三言两语地讲讲“ 三千万” 的必要。几个老乡、一个侄子— —都是维尼纶厂的干部、工人—— 先后来厂临时招待所看他。他们的话语后面, 似乎都
有张安邦的长圆脸在隐隐出现。这样的包围越多, 丁猛越气愤;而越气愤, 则越冷静。当在地委工作的几位老相识和省里的一两个老上级也用看望、捎话来表示对“ 三千万” 的关心时, 丁猛深深感到张安邦这个人物有些非同小可了! 他远不
是自己在十几年前所赏识的那个张安邦了, 那时他三十多岁, 年轻、正直、敢坚持原则, 有工作魄力, 虽然有些骄傲的缺点, 但愿意改正, 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
但现在, 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真是“ 时势造英雄” ! 丁猛一点不客气, 他警告张安邦: “ 不要搞小动作! 抓住了, 当心吃家伙! ” 张安邦对此只是不加解释地笑一笑,
那表情好象是说: 我对你丁局长哪能搞小动作呢! 丁猛也知道, 这时的张安邦, 对他进行任何言词的敲打, 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都可以一笑敷衍。现在要的是尽快查清“ 三千万” ! 丁猛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工程师钱维丛。这是他上任第一天就发现的人才。当他在轻工局一个科室的晦暗角落, 找到这位正弓背俯身子绘图板上的老工程师时, 他几乎抑制不住一种愤懑的情绪。钱维丛! 丁猛十几年前就看过他的预算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位预算专家竟然被从国家建委“ 下放” 到这儿, 默默无闻, 丢开专业改行九年了。
终于, 钱维丛来到维尼纶厂。
当钱维丛从吉普车里钻出来时, 出现在指挥部成员面前的只是一个略显驼背的身材矮小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头。“ 这就是钱工!’ 丁猛按轻工局内对钱维丛的惯称介绍道。他的样子毫不起眼, 甚至有些衰颓, 说话时有些客气得过份, 握手时头也点得过多过低。这第一面, 就让张安邦小看: 寒酸! 钱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地下降了、不过, 张安邦既善于用不卑不亢的亲敬坦然对待上级领导, 也善于用平易近人的微笑来表现对弱者的和蔼。他略挺起肚子, 很有气派地伸出手和钱工相握。他微笑着, 风趣地寒暄了几句, 又转身一一介绍了指挥部的成员们, 显出一个有威信的领导者足够的风度。
丁猛当然把来人当成圣驾。他知道这位专家一眼就能估出一座楼房的造价。当天晚上, 在厂招待所房间里和钱工面对面坐着, 丁猛就开门见山地说: “ 钱维丛挂帅卫—— `三千万, 的审查主要靠你罗! ” “ 不, 不, 要靠领导。” 钱工连忙说。“ 领导高明论? 没了群众, 左眼瞎; 没了专家, 右眼瞎! 双眼瞎的领导, 管屁用! ” 丁猛说。
看到钱工还要申辩, 他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 然后, 从抽屉里端出一摞“ 预算书” , 往桌上一放: “ 阿拉伯数字都在里头。
要听汇报, 我给你组织; 要看现场, 让指挥部派人陪你。你拍板, 我负责, 这就是咱俩的双簧! 嗯? 要几天时间够了? — —吃饭, 我给你从食堂打。”丁猛把审查“ 三千万” 的全权交给了钱工, 并在第二天指挥部的会上明确宣布: 这次审查预算, 钱工为主, 他为辅, 钱工说话是算数的。
钱工成了焦点。众目睽睽, 人们都注视着预算专家, 而这位预算专家却只是和大家客客气气地点头寒暄, 对任何预算问题都含含糊糊地回避, 他丝毫不管事!
“ 怎么办? ”和丁猛一起来审查“ 三千万” 的轻工局基建处处长着急地问。丁猛皱着眉, 没说话, 他在思索。
人们不知道: 钱工正陷入尖锐、剧烈的矛盾中。晚上, 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面对着一桌子摊开的几十本“ 综合预算书” 和计算尺、计算机, 他紧锁着眉头, 一个劲地抽闷烟, 把自己埋在腾腾的烟雾中。他在“ 预算书” 中一发现问题, 就气得猛地举起拳头, … … 然而每次又无力地落下, 叹息地摇摇头。丁猛几次推门进来, 发现钱工内心矛盾的举止, 钱工都连忙掩饰地支吾: “ 噢, 没什么。”他能对丁猛说什么呢? 对于这个被十几年动荡生活弄得不知所措, 灭了锐气磨了棱角的工程师, 丁局长从一开始就给了他以极大的温暖和信任—— 那是他曾经很熟悉, 但十几年来又生疏了的感觉—— 使他心中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的冲击。当他看到丁猛, 一个局长, 提着饭盒给他打饭回来, 点点头给他放下的时候, 他不能不感到一个预算人员的重大职责。但是, 他却又想到妻子—— 一个理解丈夫事业的家庭妇女——在自己临来前说的话: “ 到维尼纶厂少管事, 让领导作主, 要不, 更回不了北京了!” 妻子的话, 包含了他们几年来的苦恼和艰辛的体会。
为了调回北京, 回原单位, 把大半辈子的专业经验贡献出来, 老两口几年来历经奔波之苦。
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弄得他们满腹牢骚, 个别承办人员的违法乱纪更气得他们发抖!前不久, 总算熬到了国家建委来了调令, 但是到了省里、局里, 又几个月杳无
音讯。现在, 丁局长又叫他来维尼纶厂审查预算, 他刚一听到还挺兴奋, 他对本行工作有抑制不住的热情。可听到妻子一顿数落, 他明白了: 干开了, 更脱不了身! …… 他内心的矛盾, 由于张安邦的影响而更加激烈。他来维尼纶厂的第二天,
儿子小博就来告诉他: 张安邦的妻子在省委组织部工作, 他答应帮助钱工解决调动的间题。钱工一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 真要谢谢人家了!’ 没想到, 却遭到儿子的白眼: “ 谢什么!你只要把` 三千万’批了就行了! ” 为了解除他的疑虑, 儿子又
说, “ 人家当然不会这样直接说。张书记说, 你想专业对口, 发挥专长, 是人人应该帮忙的事情! 还说, 这两天我不用上班了, 专门照顾你, 有时间, 多和你谈谈, 说维尼纶厂要早日竣工, 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还不是那个意思” ? 张安邦的网又把钱工网住了。
整整三天过去了, 钱工毫无动静。
张安邦在各种场合更加轻松坦然, 谈笑风生。
指挥部的成员们纷纷说, “ 三千万” 该批了吧! 轻工局基建处的处长、副处长一天比一天焦急。
然而, 丁猛这边却悄声无息。
谁也不知道丁猛在等待什么。可是在丁猛眼里, 情况正在发生人们一般不易觉察的重要变
化。在视察工地时, 钱工的眉头开始紧锁; 沉着脸不说话的表情, 代替了他那过分的客气和过多的点头。张安邦也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当他和丁猛的目光在无意中相遇时, 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的心理。
巡视到几幢即将竣工的宿舍楼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几幢完工了, 每平米一百块钱。” 省建九处的预算员汇报道。“ 这不能叫完工吧? ” 钱工和一群人站在粉白的房间里四面看着, 他明显地克制着自己, 尽量客气地说道, “ 门窗油漆呢? 玻璃呢? 楼梯扶手呢了还有楼下的散水、厕所的上下水, 都没完
嘛! …… 你们一平米己经花了一百零九块四角九了万”
“ 噢, 造价是高了点儿。” 预算员解释道, “ 不过这几幢楼都是严格按照设计施工的, 质量比较好。”
“ 质量也不能说理想。” 钱工用力推着一面雪白的墙壁, 墙壁弹性地晃动了。
“ 隔墙是板条墙, 不是砖墙。图纸就是这样设计的! 完全照图纸的! ”
这种一而再, 再而三的辩解使钱工终于愤怒了。他双手用力一下又一下推着, 墙壁厉害地晃动起来, 白灰斑驳脱落。“ 照图纸? 有这样的板条墙设计? ” 他看到对方还想解释, 眼里更冒火了, 一手指着对方, 一手拍打着墙壁:
“ 你把图纸拿来!去!—— 拿来! 板条墙设计是有的, 你这样的板条墙, 没人会设计! 把这白灰粉刷去掉! 看看你们木料够不够设计标准! 你们至少减料三分之一! ’ 他又推了推墙, 估计了一下后纠正道: “ 可能有百分之四十… … 不要以为白灰抹住了, 就把问题掩盖了, 按规矩, 应该拆掉重做!’
辩解者满脸涨红, 全场哑然。人们看到了一个与谦卑, 客气截然相反的钱工。丁猛在心里愤愤地骂道: “ 瞎了眼了! 这些年把这些专家打在一边, 凭什么不倒退! ”
当天晚上, 丁猛来到钱工房间, 他直截了当地问。“ 怎么样, 查出问题没有?’
“ 嗯 …… ”
“嗯什么? ” 丁猛在满桌的预算书中找出好几本来, 用手拍着说:
“ 就这几个方面, 难道没有问题? ”
钱工的额头渗汗了, 犹豫着, 又摸出一支烟来。丁猛坐下, 替他划着了火柴, 老朋友一样知心地说: “ 你有什么顾虑, 尽管说, 可不敢窝在肚
里窝出病哟!”
钱工终于鼓起一点勇气说: 希望局里能放他回北京; 追加预算, 他可以帮助审查。
“ 这是做买卖? 要讲价钱? ” 丁猛一下子站起来, 虽然他昨天还专门打长途电话, 要求局里尽快研究批准钱工的调动, 但他没想到钱工现在会这样回答。
“ 把工作当成你调动的条件? 不答应你回北京, 你就不干了? ”
钱工的脸顿时红了, 疚愧不堪。
丁猛在屋里踱了个来回, 然后走到桌前, 把全部预算书探到一起, 往钱工面前一撂:
“ `三千万’ , 你签字吧, 权早就交给你了! 凭你预算家的良心。”
第二天清晨, 基建处处长推开丁猛的房门, 只见他正披着灰色的棉大衣, 手撑着额头, 侧靠着桌子一动不动地凝神坐着。灰白的曙光透过冰花的玻璃窗溶进柔黄的台灯灯光里, 照着丁猛皱纹深刻的额头。他紧紧皱着眉头, 显然是陷入沉
思许久了。
“ 老丁, 你一夜没睡? ” 处长走了进来, “ 隔壁钱工好象也一夜没熄灯。”
“ 噢… … ” 丁猛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他早已知道。
“ 是愁人哪! 到现在, 对压缩`三千万, 还毫无办法。” 基建处长感叹地坐下, “ 老丁, 你又为这苦思苦想了一夜” ?
“ 我是在想, ` 三千万’ 压缩下去以后, … … 对, 就是以—— 后—— , 我们应该如何具体争取竣工? ”
基建处长睁大了眼睛。
第二天在联合指挥部为审查“ 三千万” 召开的会议上, 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当丁猛说: “请钱工代表局里讲几句” 时, 大家都感到会议即将结束了, 一张张被烟雾罩住的面孔开始活泼起来, 人们轻松愉快地听着钱工客气的开场白, 相信“ 三千万” 的通过到了最后阶段了。
但是, 一下子几十张面孔却因为震惊而瞪目结舌了!连满屋的烟气都一下子凝结住了!什么? “ 三千万” 的追加预算与实际需耍“ 出入很大” ?…… 连张安邦也愕然了。
人们面面相觑之后, 又转而盯着“ 震源” 。
那位瘦小的钱工, 正在客气地选择着字眼往下讲: “ 我只是代表个人发表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仅供同志们参考。一人之见, 难免谬误。根据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 我有这样一个…… 印象, 预算出入—— 嗯… … 较大。当然, 我还没有做详细的计算。”
有些人开始激动了: 你不过是才用了几天的时间燎了燎么,就把我们翻来复去编制了一个多月的预算推翻了? 既是“ 初步印象” , 又“ 没详细计算”, 就凭这?……
一真是太想当然了! 张安邦一瞬的愕然早已消逝。他精细地发现了钱工说“ 出入很大” , 与“ 出入较大” 的前后变化, 同时也想到了昨天“ 板条墙事件” 中钱工怎样
被辩解激怒的情形。他仰靠在椅背上, 抬起手脆往下压了压:
“ 让钱工慢慢讲嘛! 咱们硅喇哇喇汇报了几天了。钱工既然来务加审查工作, 总不能一点儿意见都不发表吧? 钱工对维尼纶厂也是很关 心的嘛! ” 说完后, 依然微微含笑地看着对面的钱工, 目光表示出他的谦虚、坦然和对钱工的尊重与信任。
丁猛却一伸手对大家说: “ 不服气的可以顶! 有屁不要憋住。你一句, 我一句, 很好嘛!… …
是不是, 钱工? ” 他知道钱工一宿没睡和刚才说的“ 印象” 意味着什么。他要让那些漫天要价的人再激一激钱工。
有些人并没有理解丁猛与张安邦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过几年会计的省建九处的预算员龚会计, 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三十多岁, 身材瘦高, 面孔黄黑, 带副黄架眼镜, 微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闪着灵活的光。他在发言中列举了一系列程
序, 证明“ 三千万” 预算编制过程的郑重性; 他以一连串计算, 对整个“ 追加” 的必要性、精确性予以重申。最后, 他指着对面的白莎说: “ 甲方同志也详细审查了!” 按照甲、乙两方在经费问题上总是对立的普遍规律, 龚会计的这句话是最有力的
论据了。
人们开始附和龚会计的讲话了, 惟有自莎垂着眼皮看着桌面, 没有任何反应。
她没有敢正视钱工, 这个现在显得憔悴、衰老, 与十九年前判若两人的老工程师, 正是白莎一生中最尊崇和感激的一位老师! 一九六五年, 二十二岁的白莎( 那时叫李蓓) 从大学建筑系毕业, 首先参加了国家建委举办的预算培训班, 钱工就是培训班的技术讲授负责人。几天来, 自莎始终没有勇气和他相认。钱工, 直到这时还未完全消除踌躇, 说起话来左右寻找着字眼, 象是在水洼中用脚探寻着一块块露头的砖头一样。这更助长了申辩者们的气势。
正是申辩者所引用的一个个“ 精确的计算” 、一条条“ 条文的规定”, 这些“ 过硬的” 论据终于激怒了钱工。他面对的, 已经不是一张张客气相酬的面孔了, 而是一条条规定, 一个个数字。他的脸上, 谦卑的神情消失了, 他的眼睛, 射出了炯炯逼人的目光。
“ 你们乙方的管理费是怎么取的?”他开始提出第一个问题。
“ 按照国家规定, 百分之十八。” 龚会计在镜片后面翻动了一下眼球, 干干脆脆地答道, “ 没错吗? ”
“ 当然没错!”龚会计有些激动地把一本厚厚的“ 文件、条例汇编” 哗哗哗地翻到某一页, 摊开往桌上一撂:
“ 省革委七七年的文件规定:百分之十八… …七七年以前是百分之十七, 七七年以后就改成了百分之十八! 难道会有错吗? ”
这时, 有人在低声嘀咕: “改了行的预算专家, 只记得百分之十七的老定额…… ”
张安邦立刻笑着给钱工圆场: “ 钱工由于工作需要, 这几年没时间过问预算工作, 有些条文变化可能不太清楚。至于管理费提高到百分之十八嘛, 是新规定。当然罗! 如果能够争取以百分之十七取费的话, 那就更好了! ”
“ 百分之十八就是百分之十八! 怎么能随便取十七? 这不是争取不争取的间题, 国家规定就是法律! 提高不行, 降低也不行, 这是硬碰硬的事情! ” 钱工以不容置疑与反驳的口气继续讲:
“ 不清楚国家规定, 没有权利讨论预算, 龚技术员刚才讲的省革委文件是七七年三十九号, 对不对? 新的取费标准从七七年五月一日开始执行, 文件一共是五条, 最后有两点说明, 对不对? ”
全场的目光从钱工转向龚会计。龚会计抚弄着桌上的文件,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 … 可是, 那是指的土建取费标准, 对吧? ”
钱工停顿了一下, 把“ 三千万” 的预算书翻开, 指着其中一页: “ 那为什么, 这里边把化工管道的安装, 也按土建工程取费呢?……安装和土建难道是一种取费标准么? 你们难道不知道安装取费是另外的标准么? ”
“ 这样取费是有些出入… … ” 龚会计往上推了推顺着汗水滑到鼻尖的眼镜, 理虚地说。
“ 是出了, 还是入了, 要讲清楚。”
“ 当然是多了一点。”
“ 这一点是多少? 搞预算的同志应该用阿拉伯数字说话: ”
“ 这很难马上算出来, 管道品种、价格有好几种, 安装难度也不一样… … ”
“ 这是个几位数字? 前面的数字是几? 这你总应该知道吧!”
龚会计汗水淋漓, 手足无措了。
“ 我这儿有个粗略的计算, ” 钱工尽量放平口气, “ 这次安装化工管道用的不锈钢管总共三百二十吨, 根据不同规格的单价、吨数, 分别计算, 再予以总和, 是一千四百三十六万五干元。按土建取费要比安装取费多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元又这
就是你说的一点—— 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元! ”
“ 这样取费, 是指挥部同意的… … ” 狼狈不堪的龚会计喃喃道。
钱工激烈地打着手势: “ 谁同意也不行! 取费标准, 是经济法律, 硬碰硬的事情!”
会议室里变得鸦雀无声。
丁猛的目光移到张安邦脸上, 随便的口气里含着严厉: “ 指挥部同意的, 是不是请张安邦同志给解释一下啊? ”
“ 我有责任。技术上我不懂—— ” 张安邦感到了省建九处负责人投来的不满眼光, 立刻又调整了自己讲话的调子, “ — 但我一直是知道情况的, 也是同意的。省建方面有实际困难 …… 总之, 我应该负责任。”
“ 又是你负责任? ” 丁猛问。
“ 我做检查吧。”
“ 轻巧! 你知道情况, 那就是有意违反财经纪律! 这要受党纪国法制裁的!”
说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张安邦再也不能摆出独揽责任的风度了:
“ 我对详细的预算定额也不清楚… … ”
“ 那谁清楚呢? 是乙方蒙骗了你们吗? ……乙方的, 今天我不管, 有建工局管你们。高估冒算骗来的钱早晚要扎手的! 甲方的, 我这个轻工局局长要好好问问,你们都不清楚?” 丁猛锐利的目光转向白莎。
“ 白莎同志, 你清楚吗? ”
丁猛的发火使钱工倒有些不安起来, 他在一旁规劝地说: “ 搞预算工作的不学习、不懂行可不行啊户白莎黑密的睫毛低垂着微微颤了颤。 白莎, 你是不是也准备说自己不懂、不清楚呢? 那样也可以溜号。” 丁猛说。
“ 我什么也没说!” 白莎有些温恼了, 她扬了一下眼睛, 毫不示弱地顶撞道。
气氛变得更紧张了, 人们都捏着汗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白莎的性格脾气, 是大家都知道的。
丁猛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 满不在乎, 自以为是, 谁也不能说你, 是不是? … … 但你是国家编制内的干部! 吃国家饭, 你就应该工作!没有创造性, 起码也要有责任心!……” 丁猛极力放平口气, “ 你的事这儿不多说了, 咱们下去谈。下面请钱工接着谈。”
钱工看了看白莎、丁猛, 摊开笔记本一页页说下去, 指出的一项项错误, 有省建九处的, 也有很多是甲方—— 维尼纶厂的。数额从二百三十三万元很快增加到五百万元。
就这样, 一个上午, 三千万被否掉了五百万!
五
张安邦不得不把钱工放在眼里了, 他己经意识到, 钱工如果再这样查下去, 查起最近几年的预、决算, 查起库存物资, 那麻烦就更大了!张安邦可不愿去冒这个险。
张安邦挂着一脸亲切的微笑到招待所来看望钱工, 关于“ 三千万” , 他一个字也没提。他是专门来告诉有关钱工调动的消息的, 他说, 刚刚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 省委组织部很快就会批准。
张安邦的态度完全出乎钱工的意料, 钱工对他十分感激。张安邦摆着手说: “ 不算什么!… … 这主要靠组织上决定, 我不过是帮你联系联系。照理说, 用不着—— 也不应该靠个人关系去联系… … ”
他略有些感慨地说, “ 不过, 现在的人事关系, 现状你也是知道的, 没办法! … …” 他一边起身告辞一边替钱工推想道: “ 以后, 大概就是轻工局这一关需要考虑了… … 不过, 咱们再想办法吧! … …”
见钱工又表示感谢, 他摆了摆手: “ 不, 不, 我这算什么帮助, 你来维尼纶厂, 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 ……钱工, 关于预算, 可不用留情面, 该怎么卡就怎么卡。
顶多, 我们难一点。 … …难就难吧。这几年搞基建的实际困难, 钱工你是知道的。唉… … ” 张安邦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 我只是担心竣不了工啊! 一亿多资
金, 几千个工人, 撂在这儿, 形不成生产能力, 比什么浪费都严重啊!’
张安邦真正的心事, 则是对谁都不能讲的。
当他回到家靠在沙发上皱眉息索时, 女儿海燕走过来, 轻轻坐到他的沙发扶手上间: “ 爸爸, 厂里现在都说` 三千万’ 出的问题是你的责任, 是不是? 还说你和丁伯伯闹翻了, 是不是啊? ” 张安邦对女儿提这样的问题很不耐烦, 但他没发脾气—— 他对自己的独生女儿是非常钟爱的。在他住牛棚时, 只有七岁的海燕, 每天象片静静的柳叶穿过讥谓辱骂的人群, 提着饭盒给他送饭。她曾踞起脚, 为他擦去眼角的泪水。他拍了拍女儿的手说: “ 放心吧, 我和你丁伯伯一样, 也是一片好心, 想尽量节约投资 …… ” , 看到女儿调皮的眼睛, 他又说: “ 你还不相信? 爸爸还能骗你? 唉, 都是有些搞预算的同志不负责任!……” 女儿相信了父亲, 张安邦却感到很不自在。他不愿意女儿知道真情—— 那是绝对不行的, 他也不愿意骗女
儿, 他还有颗做父亲的心。
他站起来, 想踱一踱, 驱除一下心中的烦闷。从窗户看到丁猛和小博并着肩在楼下走过, 他一愣, 注意力立刻又转到了“ 三千万” 上。现在正是要紧三关, 可不能松劲啊!丁猛来找钱工, 钱工正坐在桌前独自抽着闷烟。中午, 小博和他吵了一顿, 说: “ 三千万就三千万吧, 有几个人象你这样死脑筋的!” 他不接受儿子的规劝, 但是和儿子的争吵却让他明白了:张安邦的目的还在于让他手下留情— 特别是在清仓上。张安邦讲的这几年基建的困难, 钱工是清楚的。真要竣不了工呢? 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会儿, 他知道丁猛是来谈清仓问题的, “ 丁局长……”他想说说他的顾虑, 丁猛却打断他:“我不是来做你的工作的, —— 不需要。清仓问题, 你去全盘考虑。… … 噢, 我刚才和小博聊了聊, 教训了年轻人一顿!”他坐下了, “ 我是想和你商量两件事。一件事, 咱们不应该光审查, 压缩预算, 还应该帮助制定一个确保竣工的方案。要有一系列措施!现在, 完全按定额编顶算、搞基建, 不是很容易的。”
“ 对啊! ” 钱工一下子掐灭了手中的烟。
“ 好, 这件事就说到这儿。咱们边清仓边考虑。还有件更大的事情要和你商量。现在轻纺要大发展, 往后新建扩建项目一大批 。我想请你在局里办个预算培训班, 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 学期三个月, 你看怎么样?”
“ 那当然好! 要不, 说加强经济管理, 上下没人, 还不是句空话! ” 钱工兴奋起来。这位丁局长除了不放他回北京以外, 哪条都好。
“ 钱工, 轻工局的培训班一办, 省建委肯定就眼热, 它又会把你抓去, 你可就留在省里更回不了北京罗了那可怎么办?”
“ 你不放我, 我有什么办法! ” 钱工无可奈何地说。
“ 我不放你? 好大的权力!” 丁猛幽默地点着头, 然后站起来踱了几步, 停在钱工面前, “ 不要小看人, 我没水平, 可良心还是有的, 每月领的国家饷!”他告诉钱工, 关于他调动的事, 局里已经批准, 今天上报到省委组织部了。钱工睁大眼睛, 感到太突然了!
“ 积压人才, 这个罪名我不担, 要说本位主义, 我也有一点儿。办培训班三个月, 算是轻工局向北京借用你。” 丁猛笑了, “ 至于省建委以后想要你, 我就管不着了! 我先把关系给你办走。我就不信, 这么大个省里, 就再没有人才了?”
丁猛和钱工谈完, 又去找白莎。
白莎正坐在桌前, 用手撑着脸颊, 肘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国家建委六五年预算培训班全体师生的合影。
她也不知道, 这两天为什么把它从箱底翻出来。照片上一百多人横成三排, 她穿着短袖衬衫蹲在第一排中间, 就在钱工—— 他在第二排中间坐着—— 的膝前。她那时年轻、活泼, 眼睛闪射着向往未来的亮光, 嘴角溢出热爱生活的喜悦。
在照片的背面写有一排漂亮的钢笔字:
李蓓
祝你成为中国的女预算专家。
钱维丛
那正是她当年的志向……她不过是翻出来随便看着, 她没想到, 那早已被自己嘲笑了、遗忘了的“ 幼稚” 生活, 却透过冷漠的岁月, 有些陌生地闪现出一线生动的光辉, 刺痛着她。它连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扰乱了她内心的平静……
丁猛的到来, 把白莎从恍惚中惊醒。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脸上露出冷冰冰的敌意。厂里传说丁猛把她的档案从组干科调出来了, 要整她。刚才张安邦来找她谈, 对于她的问话只是模棱两可地说: “ 组织上的事情, 还是不耍打听吧, … …
嗯……就是调档案, 那大概也是丁局长对你的关心嘛!” 这就等于证实了厂里的传说。
“ 和你谈谈工作。” 丁猛略略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素雅的布置, 就坐下了。
“ 说吧, 你有这权力。” 白莎淡淡地回答。
“ 今天来, 首先要批评你。对工作不负责, 是最大的错误。‘ 三千万’, 里有这么大的间题, 你也有责任。—— 责任多大, 以后再研究!”
“ 责任我负。要制裁, 请便!”
“ 光制裁能解决问题, 早就制裁你们了! ”
白莎嘴角露出一丝冷蔑。
“ 你过去学过预算吗? ” 丁猛放平了口气问。
“ 你去看档案!”
“ 那组织上会考虑的。” 丁猛脑子里闪过一丝警觉: 他是昨天才决定调中层以上干部档案的呀!“ 现在, 先和你谈谈。” 他严肃的目光直视着白莎。
“ 你可以看破红尘, 你也可以把你的态度归根于社会啦, 遭遇啦, 再这样晃荡下去。可这样白活下去, 你会后悔的!”
“ 我情愿! 就是这样! ”
丁猛呼地站了起来:
“ 我不相信你过去是这样!也不愿意你今后还是这样! ”
白莎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丁猛拽开椅子走到门口, 拉开门又扭回头说: “ 这两天你的工作—— : 第一, 准备帮助钱工清查库存物资, 先集中账目; 第二, 好好想想, ‘ 三千万’,
里里外外还有些什么问题!”
白莎惯有的内心平静完全被打破了!“我不相信你过去是这样… …” 她过去是什么样呢? 那照片上的她正在朝她微笑。是那恶梦般的十年生活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家庭的厄运, 对于一个青年女子, 无疑具有更大的残酷性。她不仅被剥
夺了政治前途; 而且被虚伪的热恋和势利的抛弃, 摧毁了女子的爱情和自尊, 几乎灭掉了她生的欲望。 … …正是为了遗忘过去, 她改了姓名。
十几年来的磨炼, 使她变得蔑视一切, 异乎寻常地淡漠和冷峻。
但她为什么在这几天突然失去了平静呢? ……
如果能够冷静地想想就会发现, 这种变化早就在孕育着了。虽然理想的毁灭, 爱情的蹂蹦, 是没有政策来落实的, 但是, 父亲沉冤的暗雪, 整个社会气氛的暖化, 毕竟在她心中透进了阳光… …。
第二天一早, 白莎将库存物资的账目调齐了, 默默地送给了钱工; 但是, 却没有对清查工作提供任何情况。
清理仓库的结果是: 维尼纶厂须减少积压物
资一千万元周转资金。这样, 三千万的追加又卡
掉一千万, 加上己经卡掉的五百万, 只剩一千五
百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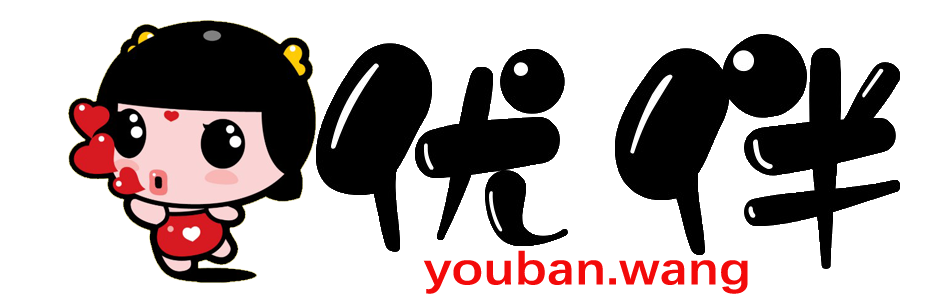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