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村子,村东头住着户穷人家,就父女俩过日子。老爹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穿针引线全靠摸,嘴里的牙也掉得差不多了,硬点的干粮都嚼不动,更别说下地干活。家里里外外全指望闺女,这姑娘没大名,村里人都叫她“穷丫头”。
穷丫头的日子过得紧巴,锅里常年见不着油星,顿顿都是稀粥配野菜。可她手脚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给老爹熬好粥,自己啃个硬窝头,然后就牵着家里那头瘦黄牛上山。
放牛的时候顺带割草,回来还得开荒种点土豆、红薯,忙到太阳落山才能歇脚。她身上的衣裳打满了补丁,蓝布的底色都洗成了灰白色,可永远浆洗得干干净净,袖口、领口都抿得平平整整,透着股利索劲儿。
村西头住着户富裕人家,也有个闺女,大伙儿叫她“富丫头”。这富丫头打小娇生惯养,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鸡鸭鱼肉,每天除了打扮自己,就是跟丫鬟们闲聊,瞅谁都带着股傲气。
有天晌午,穷丫头放牛割草回来,路过富丫头家那座青砖大院。富丫头正坐在院门口的秋千上晃悠,穿着身新做的藕荷色裙子,看见穷丫头背着半筐青草,身后跟着的黄牛甩着尾巴,一群苍蝇嗡嗡地围着牛屁股转,立马捂住鼻子,尖声尖气地喊:“哟,这是谁呀?打这儿过都能把人熏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茅厕里捞出来的呢!”
穷丫头停下脚,抬头看了她一眼。阳光照在富丫头的新裙子上,亮得晃眼,可她脸上那副嫌弃的模样,比村头的烂泥还让人不舒服。穷丫头没吭声,牵着牛绳继续往前走,草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过了几天,穷丫头割完草往家走,路过村头那片乱坟岗,瞧见草丛里露着块蓝布角。她蹲下来扒开草一看,是块半旧的粗棉布,边缘磨得有些毛糙,上面沾了些泥点子,可布料厚实,估摸着能给老爹补那条快磨破的裤子。
“真是巧了。”她笑着把布叠好塞进怀里,一路小跑回了家。院子里晾着刚洗的野菜,她找了根麻绳,把蓝布系在晾衣绳上。秋日的太阳暖洋洋的,布上的泥渍慢慢晒干,变成了浅灰色的斑块。
忽然,头顶“呼”地掠过一阵风,一只翅膀展开有半扇门宽的老鹰俯冲下来,铁钩似的爪子一把抓住蓝布,扑棱棱地往天上飞。
“我的布!”穷丫头急得直跺脚,扔下手里的木盆就追了上去。老鹰飞得不算太高,蓝布的边角在风里飘来飘去,像面小旗子。她跟着老鹰跑过村后的小河,踩着河里的石头蹚水时,裤腿全湿透了,冰凉的河水灌进草鞋;跑过长满酸枣刺的山坡,裤脚被勾出好几个洞,小腿被扎得火辣辣地疼,渗出血珠;跑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枝刮乱了她的头发,脸上划了好几道细口子,渗出来的血黏住了头发丝。可她心里就一个念头:“那是给爹补裤子的布,不能丢……”
不知跑了多久,太阳都快落到山尖上了,前面忽然冒出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老鹰扑扇着翅膀钻进云雾里,眨眼就没了影。穷丫头扶着棵老松树直喘气,胸口像揣了个风箱,呼哧呼哧响,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爹那条破裤子,又没指望补了。
正抹眼泪呢,眼前的云雾慢慢散开,露出两座紧挨着的山门。左边是座木门,木头都有些发黑了,门轴上缠着圈青藤,看着挺普通;右边是座金门,金灿灿的,阳光一照,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木门旁站着个白发老太婆,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脸上的皱纹像朵盛开的菊花,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瞅着挺和善。
“姑娘,你从哪儿来呀?”老太婆笑眯眯地开口,声音像山涧的泉水,清清爽爽的。
穷丫头抹了把脸,把老鹰叼走蓝布的事说了一遍,末了还红着眼圈加了句:“那布不值啥钱,可我爹等着它补裤子呢。”
“别急,跟我来。”老太婆领着她走到金门跟前,伸手就要推门,“先进这儿歇歇脚。”
穷丫头往后退了半步,摇着头说:“大娘,俺是穷人家的孩子,金贵地方不敢进,还是走木门吧。”
老太婆眼里闪过点笑意,转身推开了木门。门“吱呀”一声开了,里头的景象让穷丫头看直了眼:路两旁长满了从没见过的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蝴蝶在花丛里飞,翅膀扇得嗡嗡响;远处的山上有座亭子,红柱子绿瓦顶,飞檐上挂着铜铃,风一吹就“叮铃铃”响;山脚下有条小溪,水清亮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几条金红色的鱼游来游去,尾巴一甩,溅起串小水花。
“跟我来。”老太婆领着她往山里走,拐过个弯,瞧见个不大的石洞。洞里摆着两个箱子,一个是木头的,看着有些年头了,边角都磨圆了;一个是金子的,上面还刻着花纹,闪得人眼花。
“这俩箱子里装的都是布,够你穿一辈子了。”老太婆指着箱子问,“你要哪个?”
穷丫头赶紧摆手:“大娘,俺不能要您的东西,就想把俺的蓝布要回来。”
“拿着吧,算咱俩有缘分。”老太婆把箱子往她跟前推了推,“不然我心里不安生。”
穷丫头瞅着俩箱子,心里七上八下的。拿金箱子吧,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金子;拿木箱子吧,又怕辜负了老人家的好意。最后她咬了咬嘴唇,指着木箱子说:“那俺就拿这个木的,木箱子结实,能装东西。”
老太婆笑着点点头,帮她把木箱子捆在背上:“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会遇到三个水潭。第一个水潭,你洗洗头;第二个,洗洗脸;第三个,洗洗身子。记着了?”
“记着了,谢谢您大娘。”穷丫头鞠了个躬,背着箱子往前走。
走了没多远,看见个巴掌大的水潭,水清亮得像块水晶,底下的鹅卵石看得清清楚楚。她想起老太婆的话,蹲下身把头发浸到水里,手指轻轻一捋,那些枯黄分叉的头发,竟变得乌黑发亮,像墨汁染过似的,顺滑得能滑过指尖。
再往前走段路,第二个水潭比刚才那个大些,水面上漂着几片荷叶。她舀起水往脸上泼,凉丝丝的,挺舒服。抬手一摸,脸上的泥渍、划痕全没了,皮肤变得又白又嫩,像刚剥壳的鸡蛋。
第三个水潭旁边长着棵大柳树,枝条垂到水面上,两只黄鹂鸟站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唱得正欢,声音脆生生的,比村里戏班子的笛子还好听。穷丫头仰着头看鸟,没留神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水不深,刚到膝盖,她索性坐在石头上,痛痛快快洗了个澡。
等她爬上岸想拧衣裳时,忽然发现身上的破补丁衣裳不见了,换成了身淡紫色的绫罗绸缎,袖口和裙摆上绣着细小的兰花,摸上去滑溜溜的,比地主婆穿的还讲究。她走到水边一照,水里的姑娘梳着乌黑的发髻,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含着两汪水——这是自己吗?
她背着木箱子往家走,脚步轻快得像踩着棉花。到了家门口,看见老爹正坐在门槛上搓草绳,她轻轻喊了声:“爹。”
老爹抬起头,眯着老花眼瞅了半天,摇着头说:“姑娘,你找错家了吧?我闺女……没你这么俊。”
穷丫头笑了,把头发拨开,露出额头上那个小时候被烫伤的小疤:“爹,是我呀!”她把遇到老鹰、老太婆,还有三个水潭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老爹听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快,打开箱子看看!”老爹拄着拐杖站起来,手抖个不停。
穷丫头解开绳子,掀开木箱盖,里头“唰”地射出片金光——不是金子,是堆得整整齐齐的绸缎,红的、绿的、紫的,上面还镶着珍珠、玛瑙,角落里堆着几块银子,亮得晃眼。
“我的老天爷……”老爹捂着胸口,眼泪哗哗往下掉,“我闺女这是遇上神仙了!”
打那以后,穷丫头家的日子好过了。她买了两亩好地,请人把漏风的土房修成了砖瓦房,可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天不亮就起来,帮邻居家挑水,给村西头的瞎眼奶奶送吃的,地里的活计也没落下。她拿出些银子分给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教她们纺线织布,大伙儿都说:“穷丫头富了也没变心,真是个好姑娘。”
富丫头听说了这些事,气得把手里的玉簪子往桌上一摔,碎成了好几瓣。“凭啥她个穷要饭的能有这福气?”她跺着脚喊,“我倒要瞧瞧,这到底是啥门道!”
她让家里的长工去打听,没两天就把前因后果弄明白了。“不就是捡块破布,追只老鹰吗?有啥难的。”富丫头翻箱倒柜找出块最破的麻布,故意扔到猪圈旁边踩了踩,然后捡起来搭在院子的晾衣绳上。
巧了,刚搭好没一袋烟的功夫,天上就盘旋着飞来只老鹰,爪子一抓,叼着麻布就飞。“站住!”富丫头拎着裙摆追了出去,她穿着绣花鞋,跑起来一崴一崴的,没走多远就喘得不行,可一想到那些金银珠宝,又咬着牙往前跑。
追到那座大山脚下,果然瞧见两座门,一个木门一个金门,门口站着个老太婆。
“你要去哪儿?”老太婆拄着拐杖问。
富丫头翻了个白眼,撇着嘴说:“你个老东西管得着吗?我追老鹰!”
老太婆没生气,指着两座门说:“那跟我来,走哪个?”
“当然走金门!”富丫头抢在前面推开金门,里头金砖铺地,墙上挂着丝绸帘子,她眼睛都看直了。
老太婆把她领到个石洞,搬出两个箱子,一个木的一个金的。“这里的布够你用一辈子了,要哪个?”
富丫头想都没想,指着金箱子得意地说:“我才不傻呢,当然要金的!”她扛起金箱子就往外跑,箱子沉得压得她直晃悠,可心里美得冒泡——有了这箱子,全村人都得巴结我!
“姑娘,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老太婆在后面喊。
富丫头假装没听见,跑得更快了。路过第一个水潭时,她嫌绕路,直接从旁边踩了过去;路过第二个水潭时,裙子被树枝勾住了,她骂骂咧咧地扯断了树枝。
到了第三个水潭边,她实在扛不动了,把金箱子放在地上,擦着汗想:“先瞧瞧里头有多少宝贝。”她学着穷丫头的样子解开锁,刚掀开条缝,就听见“嘶嘶”的声音。
一条胳膊粗的毒蛇从箱子里窜了出来,三角形的脑袋,吐着分叉的舌头,眼睛绿油油的像两盏小灯。富丫头吓得尖叫一声,转身想跑,可毒蛇比她快多了,“啊呜”一口咬住她的脚踝。
她疼得倒在地上,看着毒蛇一点点缠上她的身子,最后张开大嘴,把她整个吞了下去。金箱子“哐当”一声摔在地上,里头滚出几块破麻布,还有些生锈的铁钉——哪有什么金银珠宝。
后来,村里人再也没见过富丫头。有人说她被毒蛇吃了,有人说她贪心太重,被神仙收走了。只有穷丫头,还像以前一样勤劳善良,跟老爹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村里的人都说:“好人有好报,这话一点不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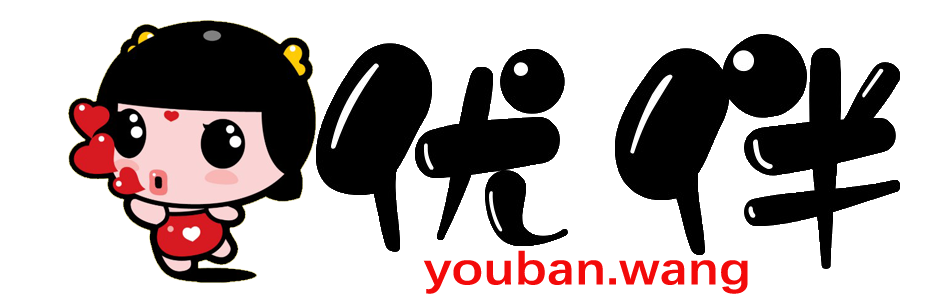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