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康定年间,汴京城有个叫沈阔的富商,字子渊,凭着绸缎生意发家,家产丰厚得能买下半条街。
他娶了柳氏为妻,两人成婚三年,恩爱和顺,待家中二老更是恭敬孝顺。只是这对年轻夫妻都已二十出头,膝下还没个一儿半女,成了沈阔心头最大的疙瘩。
那年深秋,沈阔突然得了场怪病,浑身发烫却又畏寒发抖,请来京城最有名的几位大夫,开了几十副汤药,病情始终不见好转。拖了一年多,他的身子骨日渐消瘦,连下床都得人搀扶,眼看就快不行了。
这天午后,沈阔躺在雕花大床上,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突然抹起了眼泪。柳氏正给他擦手,见他这般模样,轻声问道:"夫君这是怎么了?大夫说要静养,可别伤了心神。"
沈阔喘着气,拉住妻子的手:"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只是爹娘年纪大了,我又没兄弟,我走后谁来给他们养老?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一去,沈家就断了根了......"
他哽咽着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你还年轻,总不能守着空房过一辈子。可你若改嫁,爹娘怎么办?"
柳氏眼圈一红,掏出帕子擦了擦眼角:"夫君放心,我既然嫁进沈家,就没想过再走。你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我定会侍奉他们百年。至于子嗣,都是天意,强求不来。你别胡思乱想,安心养病才是。"
可沈阔终究放不下心。过了一个月,他的病更重了,说话都断断续续的。这天,他让仆人去把自己的同窗好友林文召来。
林文刚进房门,就见沈阔的爹娘和柳氏都围在床边,屋里弥漫着浓重的药味。沈阔挣扎着坐起身,喘着气说:"文兄,我有一事相托......我死后,你就入赘到沈家来吧。这样爹娘有了依靠,内子也不至于孤单......"
这话一出,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柳氏脸色发白,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沈阔的爹娘互相看了一眼,叹着气低下了头。
林文急忙摆手:"子渊兄,这不合礼数啊......"
"礼数哪有爹娘的养老重要?"沈阔咳了几声,从柳氏头上拔下一支金头钗,塞进林文手里,"这是信物,若日后有变故,你就拿着它去官府说清。"
林文捧着那支沉甸甸的金头钗,眼眶通红,只得点头应下。当天夜里,沈阔就咽了气。柳氏哭得死去活来,守在灵前三天三夜没合眼,水米未进,原本丰润的脸颊很快凹陷下去,看得旁人都心疼。
出殡那天,林文按沈阔的嘱托,带着个叫秦砚的书生来吊唁。秦砚是个秀才,斯斯文文的,据说是林文的远房表弟。
林文当着沈家人的面宣读祭文,说自己德薄才疏,不敢玷污沈家门楣,特荐秦砚入赘,代为侍奉二老、照顾柳氏。
沈阔的爹娘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柳氏却跪在公婆面前磕了三个响头:"爹,娘,夫君尸骨未寒,我怎能做出这等事?林兄的好意我心领了,这金头钗该还回去,让他另娶佳人吧。我这辈子就守着沈家,守着您二老。"
林文见她态度坚决,只好收回金头钗,带着秦砚离开了。
从那以后,柳氏真就像自己说的那样,悉心照料公婆,把家里的绸缎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给公婆熬粥、捶背,晚上还陪着老夫人做针线活。
街坊邻居都说沈阔没白疼她,连官府都听说了她的事迹,给她立了块"贞节牌坊",就竖在沈家门口那条街上。
春去秋来,转眼过了十年。沈阔的爹娘先后过世,柳氏按规矩为他们披麻戴孝,操办了后事。家里就剩她一个人,日子过得越发冷清。她养了只通人性的公猴解闷,那猴子浑身黄毛,眼睛圆溜溜的,柳氏给它穿上红绸小袄,平日里就拴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
那年冬天,街对面的戏班排了出新戏《牡丹亭》,邻居家的婶子拉着柳氏去看热闹。戏台上,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演得缠绵悱恻,柳氏看着看着,心里像被猫爪挠似的,有些发痒。散戏回家的路上,她低着头,脚步都有些发飘。
夜里躺在床上,柳氏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戏里的情节。她起身到院子里透气,月光照在石榴树上,那只公猴正睁着眼睛看她。鬼使神差地,柳氏走了过去,解开了猴子身上的绳子......
打那以后,柳氏就像变了个人。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素衣素服,偶尔会换上鲜亮的绸缎衣裳,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晕。只是她把院子的门看得很紧,平日里很少出门,街坊邻居只当她是思念公婆,也没多想。
半年后,包公奉命巡查汴京,听说了柳氏的贞节事迹,特意上门拜访。他见柳氏虽然已过三十,却面色红润,眼神里带着几分异样的光彩,心里不禁犯了嘀咕。离开沈家后,包公让人去打听,得知柳氏这些年深居简出,身边只有一只老猴。
第二天一早,包公让手下张龙、赵虎去沈家,把那只公猴带到府衙,拴在大堂的柱子上。过了十天,他又让人去请柳氏到府衙问话。
柳氏刚走进大堂,还没来得及跪下,赵虎就解开了公猴的绳子。那猴子一见柳氏,立刻尖叫着扑过去,抱着她的腿往上爬,爪子还撕扯着她的衣襟。
满大堂的人都看呆了。包公一拍惊堂木,怒喝道:"大胆柳氏!你平日里装得贞洁烈女一般,竟敢与畜生做出这等丑事!"
柳氏吓得面无人色,瘫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包公当即下令拆了沈家的贞节牌坊,查抄了家产。
被送回家的柳氏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想起自己十年的坚守,想起公婆临终前的嘱托,悔恨得肠子都青了。
她望着房梁,喃喃自语:"都怪我一时糊涂......"最终,她解下腰带,在沈阔的灵位前自缢身亡。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汴京,人们都说,守节难,守心更难。那座被拆掉的牌坊旧址,后来长出了一片野草,风一吹就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这段荒唐又可悲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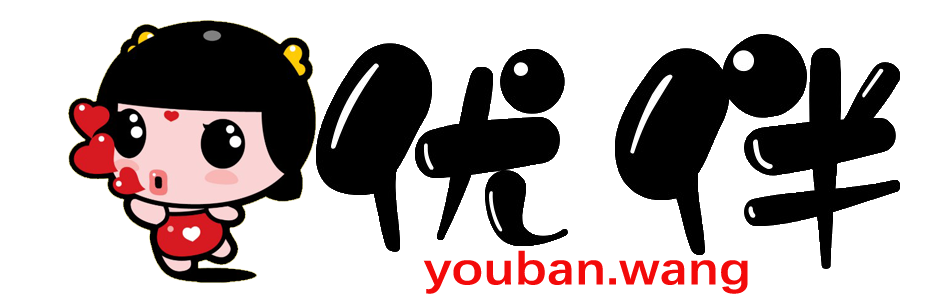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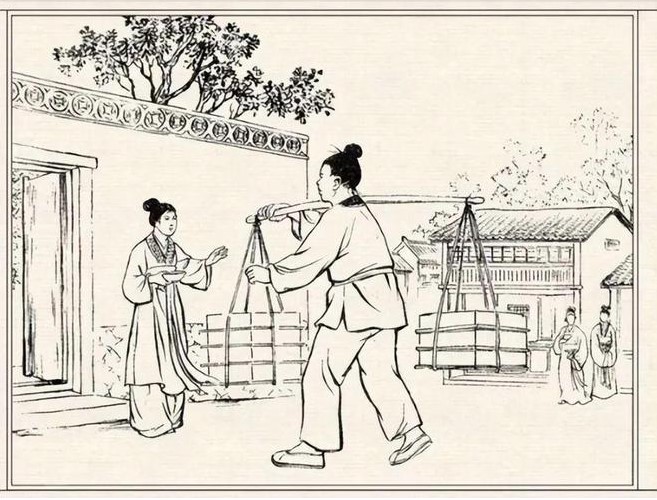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