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不大不小的村庄,名叫王家峪。这村子背靠着连绵的青山,村前一条小河常年不涸,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村里几十户人家大多姓王,世代靠着山上的几亩薄田过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槐树似的,平静里带着几分单调。
村里最靠东头的院子里,住着王老汉和他的独子王二。这父子俩的关系,村里人没一个不清楚——就像冬天冻在河里的冰块,硬邦邦的,没一点暖意。
王老汉今年六十出头,背有点驼,脸上刻着一辈子劳作留下的深皱纹,平日里总爱穿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见人不爱说话,可一说起儿子,眉头能拧成个疙瘩。王二三十来岁,身强力壮,肩膀宽得能扛起半扇猪肉,就是性子直,说话冲,跟他爹在一块儿,三句话不到准得拌嘴。
就说上个月吧,王二媳妇炖了锅排骨,想让老爷子补补身子。王二端着碗给爹送过去,刚进门就喊:“爹,趁热吃,凉了腥气。”王老汉正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眼皮都没抬:“搁那儿吧,我不饿。”王二性子急,听这话就不爱听了:“做都做了,您吃口怎么了?整天耷拉着脸,好像谁欠您八吊钱似的。”王老汉“啪”地放下烟杆:“我吃不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排骨是你媳妇回娘家带回来的,合着我吃口肉还得看你们脸色?”爷俩你一言我一语吵起来,最后王二气呼呼摔门而去,王老汉在屋里气得直哆嗦,指着门骂了半晌“白眼狼”。
这样的拌嘴三天两头就有一回,村里人见怪不怪,有时碰见了还劝两句:“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气可生?”可劝归劝,父子俩的疙瘩是越结越深。
这天晌午,日头正毒,村里的大槐树下聚着一群乘凉的老人,手里摇着蒲扇,嘴里闲扯着家常。忽然,王老汉的堂兄王老大揣着个烟袋锅子,一脸神秘地凑过来:“跟你们说个新鲜事,老王头要去告他儿子王二了!”
“啥?”有人手里的蒲扇停了,“告自己儿子?为啥呀?”
“还能为啥?说王二忤逆不孝,不养活他。”王老大压低声音,“听说老王头这几天气坏了,昨儿个在地里跟人念叨,说非让王二吃点苦头不可。”
这话像长了翅膀,没半天就传遍了全村。有人站在王老汉这边:“王二也是,年轻力壮的,多敬着点爹咋了?”也有人替王二说话:“他爹那脾气也倔,王二天天地里累死累活,回来还得受气,换谁不烦?”议论归议论,谁也没当真——哪有爹真把儿子告到官府的?
可王老汉是铁了心了。这天后晌,他揣着个布袋子,揣揣不安地往村西头走。村里的人瞧见了,都纳闷:“老王头这是去哪儿?”有人猜:“莫不是真要去写状纸?”
村西头住着个姓赵的老先生,是村里唯一读过几年书的人。据说年轻时在县城的学堂当过先生,后来年纪大了才回了村。赵老先生家里有个小书房,墙上挂着幅褪色的字画,案头摆着笔墨纸砚,村里人有个红白喜事写对联,或是邻里闹纠纷要写个调解书,都来找他。尤其是写状纸,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字写得周正,理由说得透彻,据说经他手的状纸,十有八九能赢。
王老汉走到赵老先生家门口,犹豫了半天,才抬手拍了拍那扇斑驳的木门。“谁呀?”屋里传来赵老先生慢悠悠的声音。
“赵先生,是我,王老汉。”
门“吱呀”一声开了,赵老先生穿着件干净的长衫,手里端着个茶杯,看见王老汉,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是老王啊,进来坐。”
王老汉跟着进了书房,一股墨香混着茶叶的清香扑面而来。他没心思打量这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呼呼地说:“赵先生,我要告我儿子王二!您得给我写张状纸!”
赵老先生放下茶杯,慢悠悠地坐下,打量着王老汉:“哦?告儿子?这可不是小事。你说说,他怎么不孝了?”
“他……他不把我当爹看!”王老汉越说越气,“我让他给我挑担水,他说没空;我让他买斤肉,他说没钱;那天我感冒了,想让他去请个郎中,他倒好,说我装病!您说,这不是不孝是什么?”他拍着大腿,唾沫星子都溅了出来,“我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年?他就这么糟践我,我咽不下这口气!”
赵老先生听着,捋了捋下巴上的山羊胡,点点头:“行,状纸我能写。不过,这写状纸的规矩你也知道,得要一百五十吊钱。”
“一百五十吊?”王老汉眼睛瞪圆了,“这么贵?”
“这可不是随便写写的。”赵老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这状纸递到县衙,得让县官一看就觉得你占理,立马把人抓来审问。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少了这个数,我可写不了。”
王老汉心里犯了嘀咕:一百五十吊钱,够买一头牛了。可一想到王二那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又咬了咬牙——钱没了可以再挣,这口气不出,他睡不着觉!“行!钱我给!您受累,一定把状纸写好,让县官好好治治他!”
他从布袋子里掏出个油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十吊铜钱,还有几锭碎银子——这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原本打算留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用的。他数了半天,把钱往桌上一推:“先生,您点点,不够我再想办法。”
赵老先生瞥了一眼,点点头:“够了。你明天来取状纸吧。”
王老汉这才松了口气,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又像揣着个宝贝,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他走后,赵老先生拿起那包钱,摇了摇头,没说话。
再说王二,那天在地里干活,有个相熟的邻居凑过来,压低声音说:“王二,你爹去赵先生那儿了,说要告你不孝呢。”
王二手里的锄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愣了半天,才骂了句:“他真要这么干?”他心里又气又慌——在那会儿,“忤逆不孝”可是大罪,轻则打板子,重则流放,要是真被官府定罪,这辈子就完了。
他扔了锄头,一路小跑回了家。媳妇正在院子里喂鸡,见他脸色发白,忙问:“咋了这是?”
“我爹要去告我!”王二把事情一说,媳妇也急了:“哪有这样的爹?咱虽说没天天给你爹送肉送菜,可吃的穿的从没短过他的呀!”
“说这些没用。”王二来回踱着步,“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真被抓去打板子吧?”他忽然想起什么,“对了,爹去找了赵先生,我也去找他试试!”
媳妇拉住他:“赵先生能帮你?他刚收了爹的钱……”
“死马当活马医吧!”王二甩开媳妇的手,拔腿就往赵老先生家跑。
到了赵家门口,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赵老先生还在书房里,见是他,一点也不意外,笑着说:“是王二啊,坐。”
王二没心思坐,“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赵先生,您得救我!我爹要告我,我真没不孝啊!求您给我想个办法!”
赵老先生扶起他:“起来说话。你爹要告你,你想怎么办?”
“我……我也想告他!”王二红着眼说,“他不讲道理,凭啥就说我不孝?”
赵老先生点点头:“可以。不过,跟你爹一样,也得一百五十吊钱。”
王二咬了咬牙——家里的钱刚够买种子,这一百五十吊可不是小数目。可他没别的办法,扭头就往家跑,跟媳妇商量着把家里那头正要下崽的母猪卖了,又借了几个亲戚的钱,才凑够了数。
他捧着钱回到赵老先生家,把钱往桌上一放:“先生,钱给您,您可得帮我!”
赵老先生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急得满头大汗的王二,忽然笑了:“状纸我就不给你写了。”
王二急了:“那……那咋办?”
赵老先生招招手:“你过来。”
王二赶紧凑过去,赵老先生伸出手指,在他手心里慢慢写了两个字,写完还嘱咐:“到了大堂上,不管县官问啥,你都别慌,等他问到关键处,就把这手心给他看。记住了?”
王二盯着手心,琢磨了半天,点点头:“记住了。”他心里还是没底,可看着赵老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也只能信了。
第二天,王老汉揣着赵老先生写好的状纸,兴冲冲地往县城赶。状纸是用黄纸写的,字又黑又大,上面一条一条列着王二的“罪状”:“不敬长辈,出言不逊”“春耕时不给老人送饭”“冬日里让老人睡冷炕”……条条都写得像模像样。王老汉越看越得意,仿佛已经看到王二被衙役绑着,跪在大堂上受审的样子。
县城离村子有几十里地,王老汉走了大半天,才到了县衙门口。县衙是座灰砖瓦房,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看着就威严。他深吸一口气,拿着状纸就往里走,被门口的衙役拦住了:“干什么的?”
“我……我要告状。”王老汉把状纸递过去。
衙役接过状纸,看了一眼,往里喊了一声:“有人告状!”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官服的人走了出来,是县衙的主簿。他把王老汉带到大堂旁边的耳房,问了些情况,登记在册,然后说:“你先回去,等通知。”
王老汉不放心:“大老爷啥时候审啊?”
主簿不耐烦地说:“等着就是,少啰嗦。”
王老汉只好回了村,天天盼着县衙的消息。过了三天,两个穿着黑衣的衙役真的进村了,手里拿着铁链,直奔王二家。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王二媳妇吓得直哭,王二却异常平静,跟着衙役就走了。
到了县衙大堂,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大堂上摆着一张长长的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和几支签子。县官穿着官服,坐在公案后面,一脸严肃。两旁站着十几个衙役,手里拿着棍子,齐声喊:“威武——”
王老汉站在左边,王二被铁链锁着,跪在堂下。
县官拿起状纸,看了看,又看了看王二,沉声问:“堂下可是王二?”
王二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回答:“是。”说着,往前爬了半步。
“你爹告你忤逆不孝,可有此事?”县官又问。
“回大老爷,我……”王二刚要辩解,又想起赵老先生的话,把话咽了回去,只说,“我知道。”说完,又往前爬了半步。
县官把脸一沉,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大胆王二!既知你爹告你,为何还敢忤逆?从实招来!”
王二磕了个头,慢慢抬起头:“青天大老爷,容我细说……”
“有话快说!”县官不耐烦了。
王二深吸一口气,慢慢把手掌摊开,对着县官说:“大老爷,您看这个。”
县官皱着眉,凑过去一看,只见王二手心里写着两个字:“爬灰”。他先是一愣,接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旁边的衙役都看傻了。
笑了半天,县官才止住笑,对王老汉说:“老王头,你这状纸,我看就算了吧。”
王老汉急了:“大老爷,他不孝,您咋不罚他?”
“罚啥呀?”县官摆摆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这是家事,官府不好插手。回去吧,好好过日子。”说完,也不管王老汉愿不愿意,就让衙役把他们父子俩送回了村。
王老汉一路上都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县官一看那俩字就不审了?他想问王二,可王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回到村里,这事又成了新的谈资。有人问王二:“你跟县官说啥了?咋就把你放回来了?”王二只笑不答。有人去问王老汉,王老汉也是一脸糊涂:“我哪知道?县官看了王二手心一眼就笑了,然后就让我们回来了。”
其实王二手心里的“爬灰”,在当地是句骂人的话,指的是公公跟儿媳妇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这可是天大的丑事,谁家要是沾了这事,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赵老先生料定,县官要是看到这两个字,肯定不会再往下审——真要是把这事抖搂出来,不光王老汉和王二没脸见人,连县衙都得跟着丢人,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这种丑事。
王老汉后来还是弄明白了“爬灰”是啥意思,气得差点晕过去,找到赵老先生家,指着他骂:“你咋能这么坑我?”
赵老先生不急不慢地说:“我要是不这么办,你儿子就得受罚,到时候你们父子俩的仇就结深了。现在这样,虽然难看点,可好歹没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是吗?”
王老汉想想也是,气鼓鼓地走了。
这事之后,父子俩的关系更僵了。王老汉见了王二,要么扭头就走,要么就冷嘲热讽;王二见了爹,也低着头不说话,家里的气氛比冰窖还冷。王二媳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常常偷偷抹眼泪。
村里人看在眼里,有人劝王老汉:“都过去了,别再计较了,儿子再不好,也是亲的。”也有人劝王二:“你爹年纪大了,脾气倔点,你多让着点。”可谁的话也没听进去。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到了夏天,地里的麦子该割了。王二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累得倒头就睡。王老汉呢,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就在家拾掇拾掇院子,可看着王二累得直不起腰,心里也不是滋味。
这天傍晚,王二背着一捆麦子回来,路过院子时,看见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夕阳把爹的影子拉得老长,头发白了一大半,背比以前更驼了。王二心里忽然一动,停下了脚步。
王老汉听见动静,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去,狠狠抽了口烟。
“爹。”王二憋了半天,终于喊了一声。
王老汉没应声,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了几下。
王二放下麦子,走到爹跟前,蹲下来:“爹,那天在县衙的事,是我不对。”
王老汉猛地抬起头:“你还有脸说?”
“我知道您气我。”王二低着头,“我那天不该跟您顶嘴,也不该让您生气。可我真不是故意不孝,地里的活太多,有时候忙得忘了给您送饭,您别往心里去。”
他顿了顿,又说:“村里那些闲话,您也别信。我跟媳妇商量了,等秋收了,就给您盖间新屋子,再买头驴,让您别再这么累了。”
王老汉手里的烟杆慢慢停了,看着儿子黝黑的脸和手上的老茧,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想起儿子小时候,总爱跟在自己身后,一口一个“爹”地喊着;想起儿子十五岁就下地干活,替自己撑起这个家;想起这些年儿子风里来雨里去,确实没享过一天福。
“唉。”王老汉长长叹了口气,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爹也有不对。那天不该一时冲动去告你,让你受委屈了。”
王二没想到爹会这么说,眼圈一下子红了:“爹……”
“行了,不说了。”王老汉站起身,“进屋吧,让你媳妇把饭端出来,我饿了。”
王二赶紧扶着爹,往屋里走。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把父子俩的影子叠在一块儿,看着格外亲近。
从那以后,王家峪的人发现,王老汉和王二的关系变了。王二每天下地前,都会给爹打满一缸水;王老汉呢,会坐在门口等儿子回来,有时候还会提前把饭热好。父子俩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可眼里的火气没了,多了几分暖意。
有人问王老汉:“你俩现在和好了?”
王老汉咧开嘴笑了:“儿子再不好,也是我养的。哪有记仇记一辈子的?”
也有人问王二:“你爹脾气倔,你不烦?”
王二挠挠头:“他是我爹,我让着点应该的。”
那年秋收后,王二真的给爹盖了间新屋子,还买了头小毛驴。王老汉牵着毛驴在村里转,见人就说:“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赵老先生听说了,也笑着说:“这父子俩,总算想通了。”
后来,这事就成了王家峪的一段佳话。老人们常跟年轻人说:“父子哪有隔夜仇?互相让一步,日子才能过好。”而王老汉和王二的故事,也像村口的老槐树一样,在村里一代代传了下去,提醒着每家人:亲情比啥都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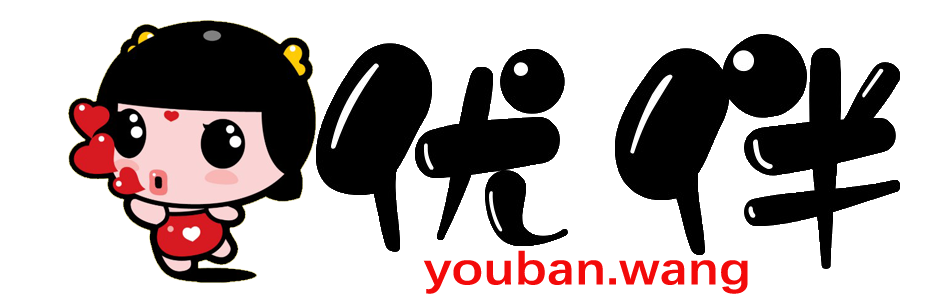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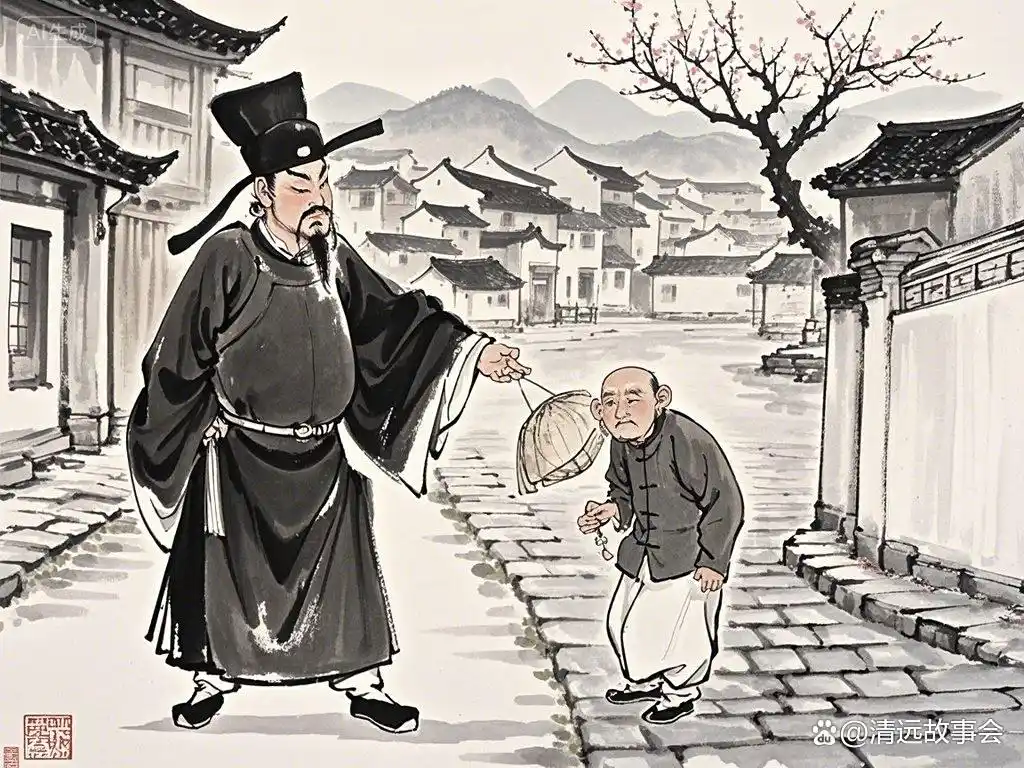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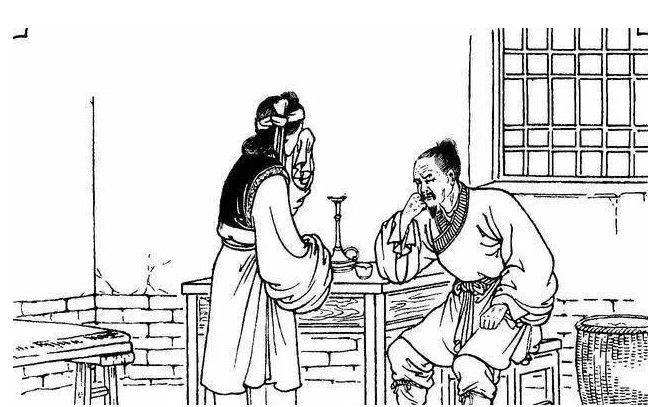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