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胶东大旱。海边的渔村晒得连蛤蜊都张着嘴喘气。刘大水蹲在自家茅草屋前,瞅着渔网上三两条小猫鱼直叹气。这光景,连海龙王都饿瘦了。
"当家的,米缸又见底了。"媳妇王氏抱着两岁的娃,眼睛红得像煮熟的虾米。刘大水挠挠头,他那脑袋跟个倒扣的海碗似的,硬茬短发里夹着几根白丝——才二十八的人,硬让生活磨成了老咸菜。
半夜里,刘大水摸黑下了炕。他抄起鱼篓和铁锹,光着脚往海边走。潮水退得老远,露出黑乎乎的滩涂。月光下,那滩涂像块发霉的糕饼,皱皱巴巴的。
"总不能饿死。"刘大水啐了口唾沫,开始挖沙蚕。挖着挖着,铁锹突然"咯嘣"一声,像是撞上了石头。他弯腰去摸,却抓出条怪鱼——通体土黄,两只眼珠子长在头顶上,鱼尾巴扁得像铲子。
更稀奇的是,这鱼离了水也不死,在沙地上扭着身子,"哧溜"就钻进了泥里。刘大水赶紧扑上去,双手扣住那处泥沙。怪鱼在指缝里乱蹿,劲儿大得像头小牛犊。
天亮时分,刘大水拎着半篓怪鱼回家。王氏吓得直往后躲:"这哪是鱼?分明是土里长的蚯蚓精!"可锅里没米,孩子饿得直啃手指头。刘大水心一横,刮鳞去脏,扔锅里煮了。
谁知这怪鱼一下锅,鲜味飘得满村都是。隔壁李老汉抽着鼻子就来了,连汤带肉吞下一碗,胡子上的油星子直晃悠:"大水啊,这'土鱼'比黄鱼还鲜三分!"
第二天逢集,刘大水煮了锅土鱼汤支摊子。赶集的人你一碗我一碗,铜钱叮叮当当往陶罐里跳。末了算账,竟挣了二百文!顶得上往日半个月的收成。
这土鱼说来也怪,专在初一十五大潮后出现。刘大水摸出门道——得在滩涂上找小鼓包,下面准藏着鱼。他做了个带倒刺的铁钩,瞅准鼓包一扎一挑,那土鱼就乖乖上来了。
转眼到了八月,刘大水家的破草房换了新茅草,娃儿手腕上还多了个银铃铛。这天他正教村里几个后生找土鱼,忽然听见马蹄声嘚嘚响。抬头一看,镇上鱼行掌柜赵德财骑着枣红马,正眯着眼往这边瞅。
赵德财这人在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算盘精"。据说他娘生他时,接生婆听见"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眼下他甩着马鞭子过来,金牙在太阳底下直闪光:"刘老弟,你这土鱼我全包了,一斤给你十五文。"
村里后生们直咽口水——市面上海鱼才卖十二文一斤。可刘大水摇摇头:"赵掌柜,俺们小门小户的,就指着这点鲜货换油盐呢。"赵德财脸一沉,马鞭子"啪"地抽在礁石上:"不识抬举!"
三天后的半夜,刘家院门突然被踹开。四个衙役提着水火棍闯进来,锁链往刘大水脖子上一套:"有人告你破坏龙脉,跟我们去县衙走一遭!"
王氏抱着孩子追出去老远,只看见火把光里赵德财的金牙一闪。她脚下一软,跪在沙滩上哭。潮水漫上来,打湿了她的青布裙子。
县衙大牢里,刘大水被问得莫名其妙。县太爷拍着惊堂木,说他挖土鱼伤了海底龙脉,要判流放三千里。刘大水喊冤,却被衙役按着画了押。牢头私下告诉他:"赵老爷说了,交出找土鱼的窍门,立马放人。"
再说王氏这边。这妇人别看平时温吞,紧要关头却像海葵似的——软身子藏着硬骨头。她把孩子托给李老汉,自己揣着几个窝头去了县衙。隔着栅栏看见丈夫满脸是伤,指甲缝里都是血,心里跟刀绞似的。
"当家的,他们打你哪儿了?"王氏眼泪吧嗒吧嗒掉。刘大水却咧嘴一笑:"没事,你记不记得上月咱家腌的那坛土鱼?"王氏一愣——那坛鱼因为太咸,一直没人吃。
回家路上,王氏的脑子转得比纺车还快。路过大集时,她特意去赵家鱼行转了转。只见柜台上摆着盆土鱼汤,标价"五十文一碗"。她假装买鱼,跟伙计搭话:"听说这鱼能钻土?"伙计得意洋洋:"可不,我们东家专门修了泥池子养着呢!"
当天夜里,王氏敲开了李老汉家的门。两个时辰后,十几个渔民举着火把来到赵家鱼行后院的泥池边。李老汉抡起镐头砸开池壁,月光下,上百条土鱼在泥浆里翻滚。
第二天升堂,赵德财摇着折扇坐在师爷旁边。县太爷刚要宣判,突然听见鼓声震天。衙役慌张来报,说上百渔民在衙门口喊冤。更奇的是,公堂地面突然拱起几个小土包,几条土鱼"扑棱棱"钻了出来!
王氏抱着个陶罐冲上公堂:"青天大老爷明鉴!民妇要告赵德财栽赃陷害!"她掀开罐子,里面是半坛发臭的咸鱼,"这土鱼离了滩涂活不过三天,赵家却说养在池子里——分明是他抓了活鱼嫁祸我男人!"
赵德财跳起来要抢陶罐,被李老汉一把拦住。县太爷让衙役取来赵家池子里的"土鱼",和滩涂上刚抓的一比——池子里的鱼鳞片发暗,根本不钻土!
原来王氏发现,真正的土鱼离了原生滩涂就会死,赵德财为了制造"刘大水到处挖鱼"的假象,偷偷在别处抓普通鱼冒充。那臭咸鱼就是证据——真土鱼腌了会变红,假鱼只会发黑。
真相大白,刘大水当堂释放。赵德财以"诬告良民"的罪名挨了四十大板,赔了刘家二十两银子。最有意思的是县太爷——退堂后偷偷拉住刘大水,讨教找土鱼的诀窍哩!
后来这"土鱼"成了当地名产。刘大水领着全村人挖鱼,晒鱼干,还琢磨出用海水养鱼的法子。如今去胶东,还能吃到"大水牌"土鱼酱。老辈人说,那鲜味里啊,藏着段"人心比鱼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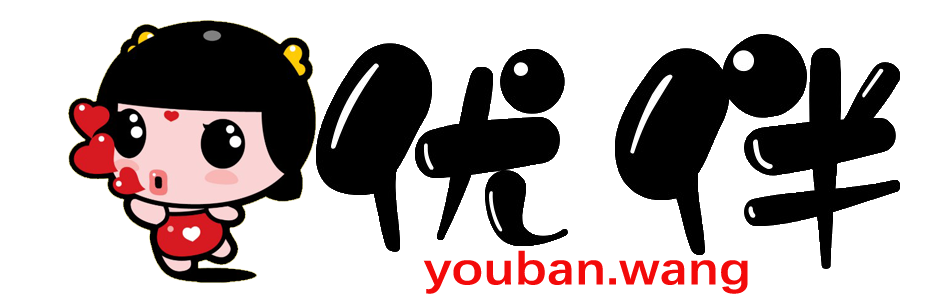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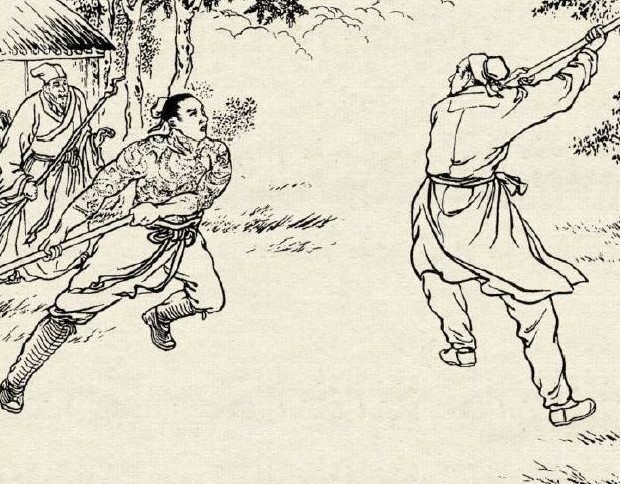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