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这么个村子,村东头住着个姓魏的老头,大伙儿都喊他魏老汉。魏老汉和老伴儿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凭着一双勤劳的手,起早贪黑地干了几十年。年轻时开荒种地,后来又跟着泥瓦匠学手艺,攒下了不少家业——前后算下来,有二十多亩良田,还有一整个四合院,连带几间临街的铺子,在村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富庶人家。
老两口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个都养得壮实。眼瞅着儿子们到了娶媳妇的年纪,魏老汉咬咬牙,给老大、老二、老三先后成了家,把三间临街铺子分了,良田也按人头匀了,自己老两口就守着四合院里最靠里的两间小屋,想着手里留几亩地养老,日子总能过得去。
可谁成想,儿子们成了家,心思就全在自家小日子上了。刚分家那阵子还好,仨儿子轮着给老两口送些吃的,逢年过节也能添件新衣裳。可过了没两年,尤其是三个儿媳妇进门后,日子就变了味。
大儿媳妇是个出了名的抠门,轮到她家伺候老人,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糊饼子,要么就是没滋没味的煮棒子,连点盐都舍不得多放。魏老汉和老伴儿牙早就掉得差不多了,糊饼子硬得硌牙,煮棒子啃起来费劲,每回吃饭都跟受刑似的。二儿媳妇更过分,觉得老两口偏心老大,送吃的时总是摔摔打打,碗底朝天就那么点东西,还得听她念叨半天“老人是累赘”。三儿媳妇年轻些,嘴甜,可手脚懒,三天两头说家里没粮,送来的野菜团子能淡出鸟来,老两口常常饿得夜里睡不着。
有回老伴儿淋了场雨,咳嗽得直不起腰,想让儿子们请个郎中,老大推说地里忙,老二说手头紧,老三干脆躲出去不见人。魏老汉没办法,自己揣着攒下的几个铜板,一步一挪地去邻村请郎中,回来时鞋都磨破了,看着病床上咳得满脸通红的老伴儿,老两口背对着背抹眼泪。
“这日子没法过了,”老伴儿喘着气说,“咱这辈子挣下的家业,全给了他们,临了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图啥呀?”
魏老汉吧嗒着旱烟,眉头拧成个疙瘩:“孩子们是被媳妇们撺掇坏了,可终究是咱的骨肉,总不能真不管咱吧?”话虽这么说,可看着窗外三个儿子家烟囱里冒出的烟,闻着那边飘来的肉香,再看看自家灶台上冷掉的糊饼子,心里头跟针扎似的。
那天夜里,老两口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院外传来老大趿拉着鞋走路的声音,像是要去茅房。魏老汉忽然眼睛一亮,用胳膊肘碰了碰老伴儿,压低声音说:“有了,我想出个法子。”
老伴儿凑近了些:“啥法子?”
“你听我说,”魏老汉附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老伴儿先是皱眉,接着点头,眼里渐渐有了光。
等老大的脚步声到了窗根底下,老伴儿故意叹了口气,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外头听见:“老头子,你还在琢磨啥呢?咱这几个儿子啊,没一个靠得住的,指望他们养老,怕是得饿肚子。依我看,不如把那宝贝挖出来,卖了钱,咱自己租个小院,雇个婆子伺候,过几天舒心日子。”
魏老汉“唉”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懊悔:“当初要不是你拦着,我早把那东西分了,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难。还好我留了一手,藏得严实,不然这会儿哭都没地方哭去。”
“可不是嘛,还是你有心眼,”老伴儿接话,“那东西值老钱了吧?真能让咱后半辈子不愁吃穿?”
“你忘了当年王掌柜说啥了?”魏老汉的声音透着得意,“他说那物件至少能换十亩良田,再加上几间大瓦房,够咱老两口吃香的喝辣的,用到下辈子都够。”
窗外的脚步声顿了一下,接着轻轻挪远了。老两口对视一眼,偷偷笑了。
其实哪有什么宝贝?魏老汉说的“宝贝”,是年轻时候在山里采草药,捡着的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石,当年确实有人出价想买,可他没舍得卖,后来搬家时早就不知丢到哪儿去了。这不过是老两口被逼急了,想出的计策。
第二天一早,老大媳妇就端着个白瓷碗来了,里头是热气腾腾的鸡蛋羹,还撒了点葱花。“爹,娘,趁热吃,”她脸上堆着笑,跟往常那副耷拉着脸的样子判若两人,“昨天的糊饼子怕是硌着您二老了,今天我特意蒸了鸡蛋羹,好消化。”
魏老汉和老伴儿愣了一下,没敢接。老大媳妇把碗往炕桌上一放,拿起旁边的脏衣服:“我看这衣裳该洗了,我拿去搓搓。”说完就端着盆往外走,路过自家门口时,还瞪了正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老大一眼。
老大赶紧掐了烟,跑进屋里:“咋样?听见了?”
“听见了!”大媳妇压低声音,眼睛发亮,“老两口真藏了宝贝,听那意思还挺值钱,王掌柜都看上了!怪不得爹当初分家产时磨磨蹭蹭,原来是留了后手!”
“那咱得好好表现啊,”老大搓着手,“等他们把宝贝给了咱,以后咱就是村里首富了!”
打这天起,老大一家对老两口的态度,那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早饭是白面馒头就小米粥,中午擀面条,卧俩鸡蛋,晚上更丰盛,时不时炖只鸡,烧条鱼,大媳妇还把自己陪嫁的布料拿出来,给老两口做了新棉袄。到了该轮老二家伺候的日子,老大媳妇拉着老太太的手不放:“娘,您在我这儿住着舒坦,再留几天呗,我刚炖了排骨,您尝尝我的手艺。”
老二看着眼热,心里直犯嘀咕:“大嫂向来把铜板看得比命都重,咋突然对咱爹娘这么大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二媳妇也觉得蹊跷:“前两天还听见她跟大哥吵架,说咱爹娘吃得多,今天就炖排骨了?不对,绝对不对。”
当天夜里,老二揣着个马扎,假装在院里乘凉,其实是想听听动静。果然,等他挪到窗根底下,又听见老两口在说话。
“老头子,老大这两天倒是勤快,你说他是不是知道啥了?”老伴儿的声音带着疑惑。
“不好说,”魏老汉慢悠悠地说,“再看看,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孝顺,等咱走了,那宝贝就给他。要是装样子,咱就给老二,好歹老二小时候跟咱亲。”
“可别给老二,他媳妇厉害,到时候怕是连口汤都不给咱剩,”老伴儿故意提高了些声音,“我看老三还行,就是年纪小,不懂事。”
老二在外面听得心头发热,原来老大是冲着宝贝去的!他赶紧回屋,把听见的话跟媳妇一说,二媳妇拍着大腿:“怪不得!我说老大咋转性了,咱也得加把劲!明天我就去买两尺好布,给爹娘做件新衣裳,再杀只老母鸡炖汤!”
第二天一早,二媳妇就提着个篮子来了,里头是刚蒸的糖包,还有一块崭新的蓝布。“爹,娘,我给您二老送早点来了,这糖包是用红糖做的,甜乎!”她把布往炕上一铺,“您看这布,做件夹袄正好,我这就给您裁。”
接下来的日子,老二家更是下了血本。给魏老汉买了新的烟袋锅,给老伴儿扯了块红绸子包头,每天的饭菜比老大家更丰盛,顿顿有肉不说,还变着花样做,今天是红烧肉,明天是炸丸子,连伺候的活儿都抢着干,生怕落了后。
老三看着两个哥哥争着对爹娘好,心里纳闷,拉着媳妇嘀咕:“大哥二哥是不是中邪了?前阵子还跟爹娘置气,现在倒跟亲儿子似的,不对劲啊。”
三媳妇是个机灵人,眼珠一转:“我去问问大嫂。”她提着一篮子野菜,假装去老大屋里串门,东拉西扯了半天,终于从大媳妇嘴里套出了话——当然,大媳妇也是故意说漏嘴的,想让老三知道了,赶紧退出竞争。
可老三听了,不但没退缩,反而来了劲:“原来有宝贝!大哥二哥想独吞?没门!爹娘最疼我,这宝贝肯定是我的!”
打这天起,老三也加入了“孝顺大赛”。他年轻,腿脚快,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买新鲜的菜,给爹娘捶背捏腿,晚上还读些话本给他们解闷。三个儿子明里暗里较着劲,今天老大送布料,明天老二买点心,后天老三就请郎中给爹娘把脉,把个四合院闹得比过年还热闹。
老两口看着儿子们忙前忙后,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儿子们见钱眼开,笑的是这法子真管用,总算能吃上热乎饭,穿件干净衣裳了。
有回轮到在老大家住,吃饭时老大给魏老汉夹了块鸡腿,讨好地说:“爹,您看我对您二老咋样?您就把那宝贝交出来吧,我保证以后天天让您吃香的喝辣的,绝不含糊!”
魏老汉放下筷子,慢悠悠地说:“老大啊,不是爹信不过你,是被你们伤怕了。等再看看,谁能一直孝顺,等我闭眼前,自然会交代清楚。要是谁敢装样子,我就把宝贝捐给庙里,给菩萨添香油。”
老大赶紧摆手:“爹,您别这么说,孝顺您是应该的,跟宝贝没关系。”可心里头却更惦记了。
老两口在老二、老三家住的时候,也被问过同样的话,都用这套说辞应付过去。三个儿子没办法,只能更卖力地表现,就怕宝贝落了别人手里。
就这么过了两年,老两口的日子舒坦多了,不仅吃得好,穿得暖,儿子们还轮流带着他们去赶集,买些时兴的玩意儿。魏老汉甚至能跟着村里的老伙计去茶馆听书,老伴儿也能跟街坊的老太太们凑在一起做针线,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可岁月不饶人,老伴儿的身子骨还是垮了,那年冬天,她咳得越来越厉害,最后没能挺过去。魏老汉送葬的时候,看着三个哭得“情真意切”的儿子,心里头五味杂陈。
没了老伴儿,魏老汉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身子一天不如一天,过了半年也卧床不起了。三个儿子这下急了,天天守在床边,端汤喂药倒是勤快,可话里话外总不离“宝贝”两个字。
“爹,您放心,后事我们肯定办得风风光光,”老大说,“您就把宝贝的下落说了吧。”
“是啊爹,”老二赶紧接话,“我都看好了,就用柏木棺材,雇八个壮汉抬,再请个戏班子,保证让您走得体面。”
老三也说:“爹,我给您选了块好坟地,风水先生说能保佑子孙后代发财,您快说宝贝在哪儿吧。”
魏老汉躺在床上,气若游丝,指了指炕边的柜子:“去,把村东头的刘老爷子请来,我有话说。”
刘老爷子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看着三个儿子长大的。等他来了,魏老汉喘着气说:“刘老哥,我怕是不行了。我那三个儿子……争着孝顺我,是因为听说我有宝贝。今天我当着您的面说清楚,那宝贝……谁把我的后事办得周全,就归谁。”
三个儿子一听,眼睛都亮了,赶紧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后事办得风风光光。魏老汉点点头,闭上眼,没再说话,当天傍晚就咽了气。
这下可热闹了,三个儿子为了“宝贝”,真较上了劲。老大说要请城里的戏班子,老二说要做纯金的寿衣,老三说要摆三天流水席,让全村人都来吃。最后吵到刘老爷子面前,刘老爷子说:“都别争了,按规矩来,棺材用柏木的,寿衣用绸缎的,请个唢呐班,摆一天席,让老人走得体面就行。”
三个儿子不敢不听,凑钱买了口最好的柏木棺材,请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唢呐班,还杀了两头猪,摆了几十桌酒席,村里人都说魏老汉这辈子值了,儿子们真孝顺。
出殡那天,三个儿子哭得比谁都凶,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多舍不得爹。
等把老人安葬好,三个儿子连歇都没歇,抄起锄头、铁锹就往老两口的屋里冲,翻箱倒柜地找起来。
“肯定在炕洞里!”老大搬开炕砖,里头只有些灰烬。
“说不定在柜子底下!”老二撬开柜子,只有几件旧衣裳。
“我看在灶台里!”老三抡起锤子砸灶台,除了些碎砖,啥都没有。
三个媳妇也没闲着,把墙皮都刮了,地都翻了三尺深,连院里的老槐树都差点被刨了,可连个铜板的影子都没见着。
“不对啊,爹肯定藏得严实,”老大喘着气说,“我记得他以前总在院角的石榴树下抽烟,说不定在那儿。”
三个儿子又冲到石榴树下,抡着锄头挖起来。挖了差不多有一人深,突然“哐当”一声,锄头碰到了硬东西。
“有了!”老大喊着,赶紧用手刨开土,露出个红漆的木盆,上面还盖着块木板,用铁丝捆着。
“果然有宝贝!”三个儿子眼睛瞪得溜圆,手都抖了,小心翼翼地把木盆抬上来,解开铁丝,掀开木板——里面没有金银珠宝,没有玉器古董,只有一个布包。
打开布包,里头是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魏老汉歪歪扭扭的字。三个儿子都不识字,赶紧拿着纸条往村西头的学堂跑,找教书的先生念。
先生接过纸条,看了看,又看了看满脸急切的三兄弟,忍不住笑了,清了清嗓子念道:
“红盆扣红盆,并无金和银。爹娘定计哄儿孝,只为混账转性人。若问宝贝何处有,床头尚有救命钱,分与三家买良心。”
三兄弟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先生叹了口气:“你们爹哪有什么宝贝?他是怕你们不孝顺,才想出这个法子。他说床头还有点钱,让你们分了,买个良心。”
三个儿子面面相觑,想起这两年对爹娘的好,全是为了那不存在的宝贝,想起以前对爹娘的刻薄,想起爹出殡时自己假惺惺的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等他们回到家,果然在床头的柜子里找到了一个布包,里面只有几十块银元,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好过日子,善待妻儿,别学我年轻时只知挣钱,忘了疼你们娘。”
那天晚上,魏家四合院的三个屋里都亮着灯,没一个人说话,只有隐隐的抽泣声飘出来,不知道是哭那被骗的自己,还是哭那个用心良苦的爹。
后来,村里人常拿这事儿当例子,教育自家孩子:“孝顺不是装出来的,人心换人心,你对老人好,老天爷都看着呢。”而魏家三兄弟,虽然没找到宝贝,却真的变了性子,对媳妇和睦,对孩子耐心,逢年过节去给爹娘上坟,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半天,像是在听爹说那些没说完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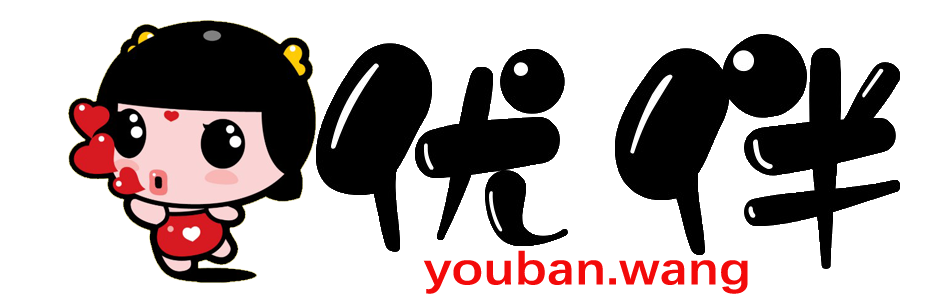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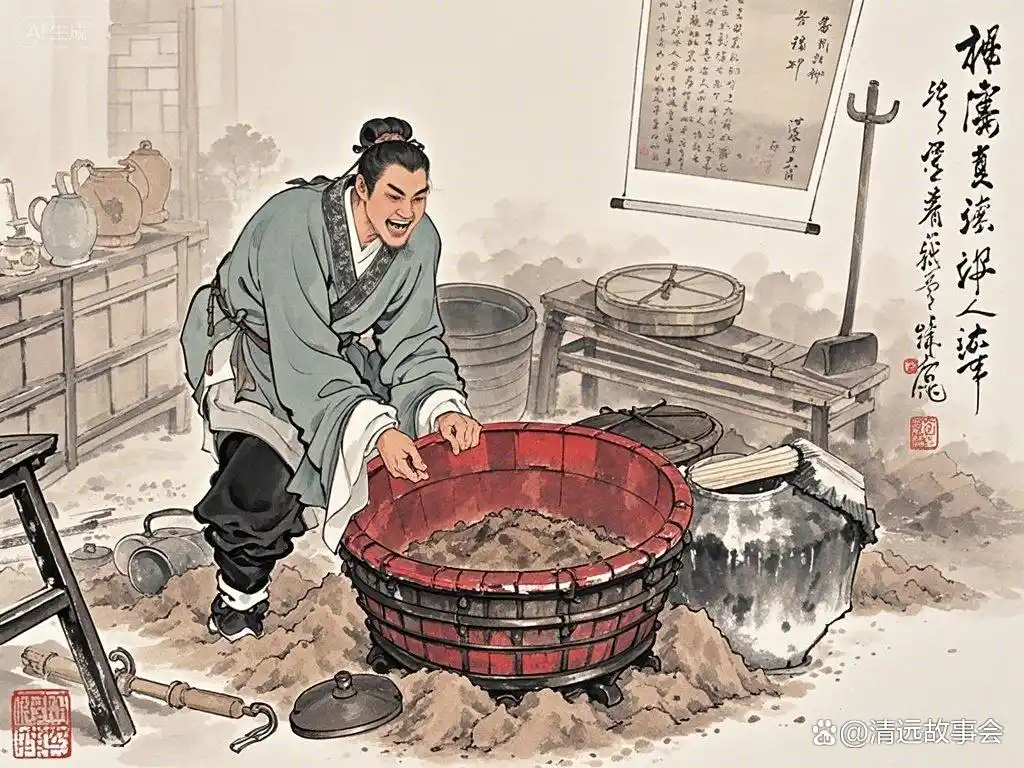




发表评论